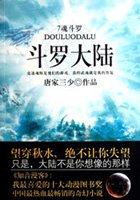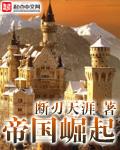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从离婚开始的文娱 > 第一千四百三十八章(第3页)
第一千四百三十八章(第3页)
王乐天读完,久久不能言语。
他将这一页扫描上传,命名为《遗声计划?第十七号证词》,并在文末写下:
>“一条路的诞生,往往伴随着无数条生命的终结。
>可我们总是记住路,忘了走路的人。
>今天,我把刘志远的名字刻在这里,不是为了悲伤,而是为了提醒:
>每一次通行,都应心怀敬畏。
>因为脚下的平坦,曾是别人的深渊。”
夜深,小月已入睡。林晚在客厅整理旧相册,忽然叫他:“你看这个。”
他走过去,见她指着一张泛黄的照片: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,一群年轻人站在大学礼堂门口,意气风发。其中一人正是年轻时的父亲,身旁站着几个同学,脸上洋溢着理想主义的光芒。
“这是我爸毕业照。”她说,“他本来可以留在北京,可他非要回西北搞电力建设。别人劝他,他说‘那边更需要人’。”
王乐天凝视着照片,忽然明白了什么。
原来,他所做的一切,并非凭空而来。那些坚持、那些不甘、那些对真相的执着,早就在血脉里埋下了种子。父亲用一生点亮了戈壁的灯,而他,只是接过了那束光,试着照亮更多黑暗的角落。
第七十六天,他接到一个视频通话请求。对方是云南麻栗坡县一所乡村小学的校长。屏幕上,几十个孩子整齐地坐在教室里,身后黑板上写着六个大字:“我们可以跑了”。
校长说:“我们组织学生观看了《奔跑的权利》,孩子们写了作文。有个孩子说,他再也不怕踩雷了,因为他知道了怎么识别危险区域。还有个女孩说,她长大要当扫雷兵,保护大家。”
接着,一个小男孩站起来,大声朗读自己的作文:
>“我的梦想是当运动员。以前我不敢跑,怕摔跤,怕疼。但现在我知道,只要路上没雷,我就敢冲。
>小满姐姐能跑,我也能。
>等我拿了冠军,我要把奖牌送给王叔叔,因为是他告诉我们??
>奔跑,是每个人的权利。”
视频结束,王乐天坐在桌前,泪流满面。
他知道,这场战斗还远未结束。三?七厂的问题才刚刚揭开一角,还有上千个名字等待被提起;边境雷区仍未彻底清除;更多像刘志远一样的无名者,仍在等待有人为他们发声。
但他不再感到孤独。
因为他看见,火种已经点燃。
在教室,在工地,在病房,在田野;
在每一个曾被遗忘的角落,都有人开始说话,开始记录,开始追问。
第七十七天清晨,阳光如约洒进书房。
他打开文档,新建一页,标题写下:
**《遗声计划?第二季:灯火长明》**
正文第一句是:
>“我们无法让时间倒流,也无法让死者复生。
>但我们能让记忆醒来,让名字回归,让牺牲不再沉默。
>这不是终点,而是起点。
>我将继续行走,继续记录,继续为那些不曾被听见的声音,搭建一座永不关闭的讲台。”
窗外,老梅树的新叶在风中轻轻摇曳,仿佛也在回应。
他按下保存键,端起茶杯,喝了一口温热的茶。
春天,真的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