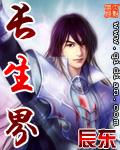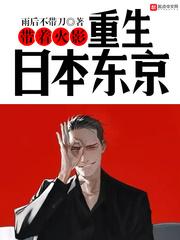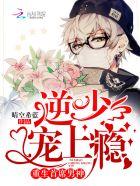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我的一九八五 > 第一八三七章 葡萄牙队不敢消极迎战(第1页)
第一八三七章 葡萄牙队不敢消极迎战(第1页)
D组第二轮比赛结束。
葡萄牙队2场全胜,积6分,率先出线;中国队1胜1负,积3分,净胜球为0,总进球4个;墨西哥队1平1负,积1分,净胜球为-1,总进球2个;安哥拉队1平1负,积1分,净胜球为-。。。
车队驶出广西小镇,沿着蜿蜒的省道向北推进。窗外是连绵起伏的喀斯特地貌,石灰岩山峰如刀锋般刺向天空,稻田在山脚铺成一片片绿绸缎。孙健靠在副驾上,手里摩挲着那片阿?给的树叶,耳边循环播放着五指山黎族阿婆最后唱的那段古调。
旋律低回、苍凉,像从大地深处升起的叹息。
“你听不厌?”林妍坐在后排,递来一瓶水,“这歌我听了三遍就睡着了。”
“不是听不厌。”他笑了笑,把耳机分给她一只,“是在听‘时间’。你能想象吗?一百年后,有人戴上耳机,突然听见一个九十二岁的声音,用没人懂的语言唱着祭祀祖先的歌??那一刻,历史就不再是书上的字,而是活生生的呼吸。”
林妍没说话,只是轻轻点头。她知道,这种东西无法用逻辑解释,只能用心去接住。
傍晚时分,他们抵达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一个偏僻村落。这里地势高峻,通讯基站常年失修,PENG信号断断续续。村口立着一块斑驳的石碑,刻着“龙潭寨”三个字,旁边还有一行小字:**1952年建寨,人口最盛时三百七十六人,现余八十九。**
“空心村。”小赵调试设备时低声说,“年轻人全走了,剩下老人和几个留守儿童。”
当晚,他们在村委会临时腾出的会议室安营扎寨。晚饭是村民送来的腊肉炒蕨菜和红薯饭,味道咸重却暖人。饭后,村长老杨点燃一盏煤油灯,脸上沟壑被火光映得忽明忽暗。
“我们这儿有个规矩。”他说,“每年清明,家家户户都要对着祖坟喊话,说是怕先人听不见后辈的声音,魂灵回不了家。”
孙健心头一震:“所以……你们一直都在‘喊’?”
“对。”老杨点头,“可这几年,喊的人越来越少。腿脚不行了,嗓子也哑了。去年清明,整个寨子只响了一声‘爹,我好着呢’,还是个小孩喊的。”
会议室陷入沉默。
孙健缓缓打开PENG终端,调出“声音邮局”的界面。
“能不能让我们录下来?”他问,“不只是清明那天的话,还有平时想说的……比如今天吃了什么,孙子考了多少分,天气好不好。我们可以设定每年清明自动播放,让机器替他们‘喊’。”
老杨盯着屏幕看了很久,忽然起身,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:一位穿蓝布衫的老妇人抱着孩子,站在老屋门前。
“这是我娘。”他嗓音沙哑,“她走前最后一句话是‘记得给我烧双布鞋,那边路远’。”
顿了顿,他又说:“我没烧。忘了。”
孙健静静听着。
“如果那时候有你们这个机器……”老杨眼眶红了,“我就能把她的话录下来,让她亲口告诉我该怎么做。”
那一夜,团队彻夜未眠。他们在PENG系统中新增了一个功能模块:“**代际回声**”??允许用户上传语音,并绑定特定节日或天气条件(如“每逢下雨”“每到除夕”)自动触发播放。同时接入本地广播喇叭网络,让逝者的声音能在村中特定地点重现。
第二天清晨,第一位来录音的是位七十多岁的独居老人。他拄着拐杖,在志愿者搀扶下走进临时录音棚。
>“妈,今天是你生日。我给你煮了碗长寿面,放了两个荷包蛋……你还记得不?小时候你总说,吃蛋聪明。”
>“我老了,记性不好,但你的样子我一直记得。你走那年,我才八岁……”
>“现在我也当爷爷了。你重孙子叫石头,皮得很,像你当年打我的竹条一样倔。”
录音结束,老人久久不愿起身。他问:“真能每年都响一次?在屋门口?”
“能。”孙健握住他的手,“只要电不断,风不毁线路,您的声音就会一直在那儿。”
老人点点头,抹了把脸,蹒跚离去。
接下来三天,几乎全村老人都来了。有人录下对亡妻的道歉,有人留下给未来曾孙的祝福,还有一个小男孩,对着麦克风大声说:
>“爸爸!妈妈说你要回来过年!我说你要是再不回来,我就把你存的钱全花掉买鞭炮!……但我其实是想你了。”
孙健听得鼻子发酸。他悄悄标记这条录音为“亲情唤醒案例”,并推送给全国流动人口聚集城市的社区服务中心。
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清晨,PENG突然弹出一条异常数据流:
>【情感脉冲异常|来源:本机缓存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