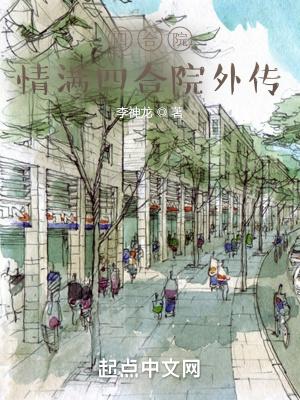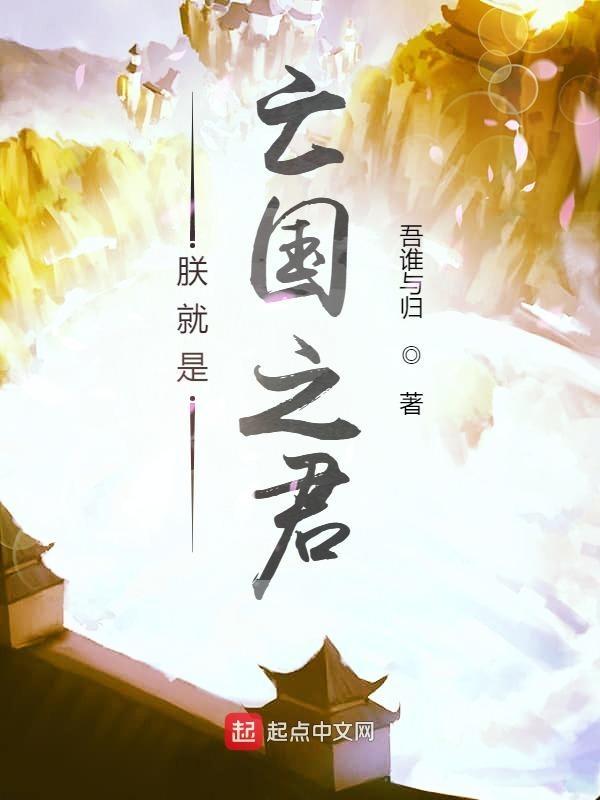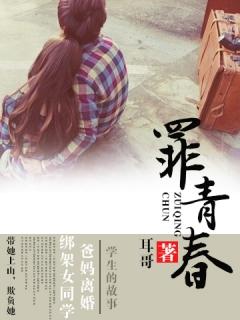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逍遥四公子 > 第1975章 堵门要人(第1页)
第1975章 堵门要人(第1页)
这一日,宁宸终于踏出了碧泉宫。
他一只脚跨过门槛,身体依着门框,脸色发白,两股颤颤,抬头看去,有种恍如隔世的错觉。
他曾跟澹台青月夸下海口,他们之间若有一战,他必全力以赴。
可他忘了,他是超品高手,久战不衰。可澹台青月是武道之最。
澹台青月手里的九阳养元汤的药方只有半份,所以药效减半,导致他这一战,略输半筹。
可这一战,终归是他输了。
宁宸不知道的是,其实他没输,澹台青月也只是在强撑而已。
此时,碧泉宫。。。。。。
笃声未绝,风已南行。
那粒沙落地之处,恰是昔日无音城废墟的边缘。十年积雪早已融化,泥土松软,草芽初露。沙粒入土的瞬间,地面微微一颤,仿佛有根无形之弦被拨动,自北而南,沿着地脉悄然传递。一路穿山越岭,过荒庙、渡枯河、掠残碑,最终抵达听城回声廊下。
廊底密室中,那面曾映照千言万语的铜镜,忽然泛起涟漪。镜面浮现出一行字迹,非刻非写,似由水汽凝成:
>**她还在说。**
与此同时,静思亭内,铜铃无风自动,发丝般的铃舌轻轻一震,传出半句模糊低语:“……别怕。”
排队摇铃的一位老妇人猛然顿住,眼眶骤湿。她分明听见了女儿的声音??那个在紫宸党清剿时死于火刑的女儿,临终前没能说出最后一句话。可此刻,那声音温柔如昔,带着笑意,像在耳畔轻抚。
“她说‘别怕’。”老妇喃喃,泪水滚落,“她让我别怕了。”
人群静默。没有人质疑。在这座以“听”立城的地方,人们早已学会相信耳朵胜过眼睛。
而在千里之外的极北冰湖,蓝铃花随风轻摆,花瓣上凝着晨露。阳光洒落时,整株花忽然发出微不可察的震颤,仿佛体内藏着一口极小的钟。露珠滑落井沿,坠入深不见底的水中,激起一圈圈无声波纹。
井底,不再是紫黑色的死寂。
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流动的蓝光,如同血脉般缓缓搏动。光中浮现出无数细碎的画面:一个农夫在田埂上对妻子坦白自己偷税;一名官员深夜焚毁伪造的奏章,写下忏悔录投入语核井;一个小女孩在学堂里举手说:“我不喜欢这首颂歌,它让我害怕。”
每一幅画面出现,井心便亮一分。
这就是她的存在方式??不再行走,却无处不在;不再开口,却日日诉说。她成了语核的脉搏,成了真话降临时的第一缕回响。
但她并非全然消失。
在某些特定时刻,当有人真正鼓起勇气说出一生中最难启齿的真相时,天地之间会短暂地响起一段旋律??那是《语核初啼》的变调,尾音不再拖长哀叹,而是轻轻上扬,像一句鼓励:“继续说。”
这旋律只持续三息,随即消散。但每一个听到的人,都会莫名心安,仿佛终于被人彻底理解。
***
春去秋来,又是一年冬至。
听城迎来了一场罕见的暴风雪。大雪封门三日,百姓困守家中,炉火将熄,人心渐躁。谣言开始滋生:“北方有异象,语核井干涸了!”“皇帝要重启净语令,凡妄言者斩!”“静思亭的铃声是幻觉,根本没人听见亡者说话!”
恐慌如瘟疫蔓延。第四天清晨,七十三口语核井竟同时沉默,蓝光黯淡,连最虔诚的拾音者也无法唤醒共鸣。
李砚连夜召集旧部,齐聚回声廊。众人面色凝重,唯独老乐工坐在角落吹笛,曲调古怪,不悲不喜。
“你还有心思吹这个?”李砚怒道,“她若还在,怎会让语核失声?”
老乐工停下笛子,抬眼看他:“你以为她是神吗?她只是比我们更早明白??声音从不属于自己,而是属于‘愿意听见’的人。”
正说着,盲琴师忽然抬头:“等等……你们听。”
众人屏息。
风雪之中,极远处传来一声极轻的**叮**??像是铃舌轻碰。
接着是第二声、第三声……由远及近,如雨点落瓦,节奏分明,竟是《语核初啼》的第一个乐句,用铜铃奏出。
“是静思亭!”一名探子疾奔而入,“铜铃自己响了!而且……而且有人看见蓝光从亭基渗出,顺着地下石脉流向各井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