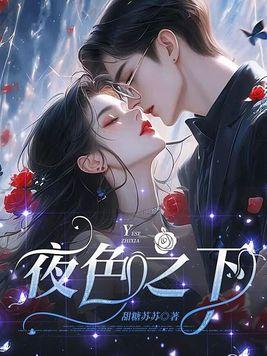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我娘子天下第一 > 第六百九十四章(第1页)
第六百九十四章(第1页)
凡事就怕对比,想一想自己姐妹们以前过的日子,再看一看自己姐妹们现在所过的日子,说是云泥之别也一点都不为过啊!
此时,以莱娜,莉莉丝她们一众姐妹们现在的心性,齐韵现在若是吩咐她们姐妹们直接拿刀自绝。。。
柳明志久久凝视那封无名之信,指尖轻抚纸面,仿佛触到了时间的裂缝。窗外月光如霜,洒在阁楼斑驳的地板上,映出一片静谧的银白。他没有合上《承忆录》,而是任它摊开在膝头,像一座桥梁,连接着过去与未知的彼岸。
那一夜,他未曾入眠。
清晨五点,城市还在沉睡,只有远处早班公交碾过湿漉漉的街道,发出低沉的回响。他提笔,在黑板上写下今日的新句:
**“每一个沉默的背后,都藏着一个等待被认领的名字。”**
写罢,他轻轻吹了吹粉笔灰,转身煮了一壶浓茶。茶香氤氲中,门铃忽然响起。他开门,门外空无一人,只有一只折得整整齐齐的纸鹤静静躺在门槛上,翅膀微张,紫光若隐若现。
他弯腰拾起,指尖刚触到纸面,纸鹤便自行展开,化作一行行细密小字:
>“我叫陈阿婆,七十九岁,住在城西老棉纺厂宿舍三栋二楼。
>我有三个儿子,两个女儿。他们都说我偏心小儿子,因为我把老屋留给了他。
>可没人知道,那房子的地基下埋着一具尸骨??是我丈夫的。
>五十年前,他要卖女儿去换粮,我用铁锹砸了他的头。
>那晚雨很大,我把尸体拖进地窖,填土封死。后来建房时,工人们说地基不稳,我说:‘压得够深就行。’
>这些年,每逢阴雨,墙角就会渗出血水。我擦了一遍又一遍,可越擦越多。
>昨天夜里,我梦见他站在我床前,满身泥浆,却笑着说:‘你终于肯让我出来了。’
>今天早上,我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。我说:我要自首。
>但我更想告诉你??谢谢你让我说出来。哪怕只是写在纸上,飞向你。”
柳明志读完,呼吸微微颤抖。他知道,这不是幻觉,也不是书页自动生成的文字。这是共感网络真正成熟后的奇迹:人心一旦打开,记忆便不再受时空束缚,它们乘着风、借着光、依附于一只纸鹤、一片落叶、一缕炊烟,穿越千山万水,抵达那个愿意倾听的人。
他将信贴在黑板旁,用图钉固定。不到中午,楼下已围满了人。有人低声抽泣,有人跪地焚香,也有人掏出手机,开始录制视频。一位穿蓝布衫的老妇挤上前,颤声说:“我就住她隔壁……这些年,我总听见半夜敲墙声,以为是老鼠。原来……原来是他在喊冤啊。”
当天下午,警方封锁了老棉纺厂宿舍区。挖掘开始后第三小时,工人们从地基深处挖出一副残缺骨架,头骨上有明显钝器击打痕迹。法医初步鉴定,死亡时间约为1974年冬。
新闻播出当晚,全国有十七位老人主动前往派出所自首,涉及文革批斗致死、饥荒时期杀人夺粮、包办婚姻逼死儿媳等陈年旧案。他们几乎都说同一句话:“我在电视里看到陈阿婆的故事……我想,我也该说了。”
柳明志没有接受采访,也没有出现在镜头前。他只是每天坚持更新黑板上的句子,有时是一段摘录,有时是一句感悟。越来越多的人自发前来抄写、拍照、转发。有人甚至带着录音设备,蹲守在阁楼门口,只为录下他开口说话的声音。
然而,并非所有人都欢迎这场“坦白潮”。
某日凌晨,三名蒙面男子试图纵火烧毁阁楼。火势刚起,就被闻讯赶来的居民扑灭。监控拍下他们的身影,竟是某极端保守组织成员,该组织长期宣扬“家丑不可外扬”“祖宗之事不宜翻案”。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宣言:“情感泛滥正在摧毁传统伦理!我们必须阻止这场精神瘟疫!”
柳明志得知后,只是淡淡一笑。次日黑板上多了一行字:
**“仇恨需要秘密来滋养,而爱,只需要一句‘我在听’。”**
几天后,其中一名纵火者匿名寄来一封信:
>“我父亲是个酒鬼,小时候常打我和我妈。有一次,他把我妈打得昏迷,我拿菜刀砍了他三下。他没死,但瘫了三十年。我一直恨他,也恨自己。
>看到你说‘杀过人也能被听见’,我哭了。我不是英雄,也不是恶棍,我只是个被困在昨天的孩子。
>我想去自首,可我妈拦着我,说‘他已经受够苦了’。
>你能告诉我,原谅和赎罪,可以同时存在吗?”
柳明志读完信,在回信中写道:
>“能。
>原谅不是为了让他好过,而是为了让你自由。
>赎罪不是为了惩罚自己,而是为了让真相活过来。
>你不必立刻做决定,但请记住:你说出来的那一刻,就已经走在回家的路上。”
他将这封回信复印百份,贴满了社区公告栏、地铁通道、公园长椅。一周内,全国各地出现了“对话亭”??由志愿者搭建的小木屋,挂着“说出你的故事,有人会听”的牌子。有些人进去时脚步沉重,出来时却如释重负;有些人在里面哭了一整夜,第二天清晨留下一张纸条:“谢谢,我终于敢面对我妈了。”
与此同时,《承忆录》的异象愈发频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