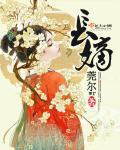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青葫剑仙 > 第两千五百四十八章 再见天音(第2页)
第两千五百四十八章 再见天音(第2页)
***
三个月后,一场名为“记忆伦理峰会”的国际会议在昆仑旧址召开。来自各国的学者、术士、忆行遗孤齐聚冰川裂谷之间,围绕如何守护新生的记忆网络展开辩论。有人主张建立“真忆防火墙”,用阵法封锁虚假信息传播;有人提议推行“共忆契约”,强制公民每日讲述一段家族往事以维持心灵连接。
争议最大者,是一位年轻科学家提出的“反向溯源计划”??利用现代灵能共振技术,逆向追踪虚噬残留意识,主动进入其源头进行净化。此议遭多数人反对,认为此举无异于打开潘多拉魔盒,可能唤醒更深沉的遗忘之力。
争论正酣时,盲女的徒弟??那个曾搀扶她出席无声寺大会的少年??突然起身。他已不再是昔日稚嫩模样,眉宇间透着沧桑与决然。
“你们都在讨论如何防御、如何记录、如何传播。”他声音不高,却压下了全场喧哗,“可你们忘了最重要的一点:记忆的本质,不是保存,而是选择。”
众人沉默。
他缓缓解开衣领,露出胸口一道贯穿伤疤,形状宛如断裂的锁链。“我在第七个心灯之夜死过一次。”他说,“那时我看见了‘它’的真相??虚噬并不是敌人,它是结果。是我们千百年来对痛苦的逃避、对责任的推诿、对真相的恐惧,共同孕育了这个怪物。”
他指向北方:“我要去戈壁深处,找那座湮灭古城。地图早已显现,只是没人敢走。传说那里埋着《囚心赋》原稿,记载着正统司最初的誓言:‘宁负天下人,不负江山稳’。但我也听说,那里藏着另一本书??《启明录》,写的是第一个拒绝篡改史册的正统司官员,在临刑前刻于石壁的遗言。”
“你一个人去?”有人问。
“不是一个人。”他微笑,“只要还有人愿意听我讲故事,我就不是独行。”
当晚,他独自踏上征途。风沙漫天,星辰黯淡。可在千里之外的江南小镇,一位老人忽然醒来,拿起毛笔,在泛黄宣纸上写下:“今日有少年西行,携火种入荒漠。”而在北方牧场,牧童梦见自己牵着一匹无主黑马,奔跑在无边沙海之中。南海渔船上,老渔民对着月光哼起一支陌生小调,歌词竟与少年幼年所唱儿歌一字不差。
他知道,自己并不孤单。
***
十年光阴如水流逝。
世界早已不同。忆馆不再是封闭殿堂,而是开放广场。人们不再被动接受“官方历史”,而是每天都在创造新的集体记忆。学校不再考试背诵,而是举办“口述节”,孩子们轮流上台讲述祖辈的故事。电视新闻开头第一句话永远是:“今天,我们想记住一个人??”
那位科学家最终完成了“反向溯源装置”,并在实验中意外发现:所谓虚噬,并未真正消亡,而是分裂成亿万微粒,寄居于每个人的潜意识中。它们不攻击,也不吞噬,只是静静等待??等待下一次人类主动选择遗忘。
于是人类学会了一项新仪式:每年清明,全民闭眼冥想一刻钟。这不是祭祖,而是自我审视。每个人都要面对内心最深处那段不愿回想的记忆??亲人的背叛、自己的懦弱、时代的暴行??然后轻声说一句:“我记着你。”
只有完成这一仪式的人,才能在额头上点一抹青墨,称为“言归印”。据说,拥有此印者,死后灵魂不会散逸,而是汇入源井,成为守护记忆长河的一缕微光。
至于青衣人梁言,再无人见过其真容。但他留下的铭文已融入大地经纬,每逢雷雨之夜,山川河流都会隐隐发光,勾勒出那两句话的轮廓。南极科考站的仪器记录到,地球磁场正发生微妙偏移,方向直指昆仑旧井。科学家们称之为“文明觉醒指数”,因为它与全球口述历史增长率高度同步。
又是一个春日。
新建的“青葫小学”里,孩子们围坐在老教师身旁,听她讲一个关于草铃与莲花的故事。讲到盲女投入花瓣那一刻,窗外忽然刮来一阵清风,带来几片不知何处飘来的花瓣,落在课桌上,竟隐约浮现字迹:
>“她说不必找我,
>可我还是来了。
>因为你说的故事,
>正是我回家的路。”
孩子中有个小女孩伸手接过花瓣,甜甜笑道:“老师,我昨晚梦见一个穿青衫的哥哥,他说谢谢我昨天给爷爷录了口述日记。”
老师怔住,随即含泪点头。
铃声响起,放学了。孩子们蹦跳着奔向校门,书包上挂着自制的小铃铛,叮当作响。风穿过校园,拂过旗杆,一只青鸟悄然落下,嘴里衔着一片新叶。
叶上无字。
但它不需要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