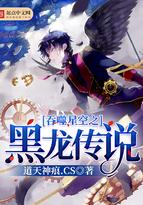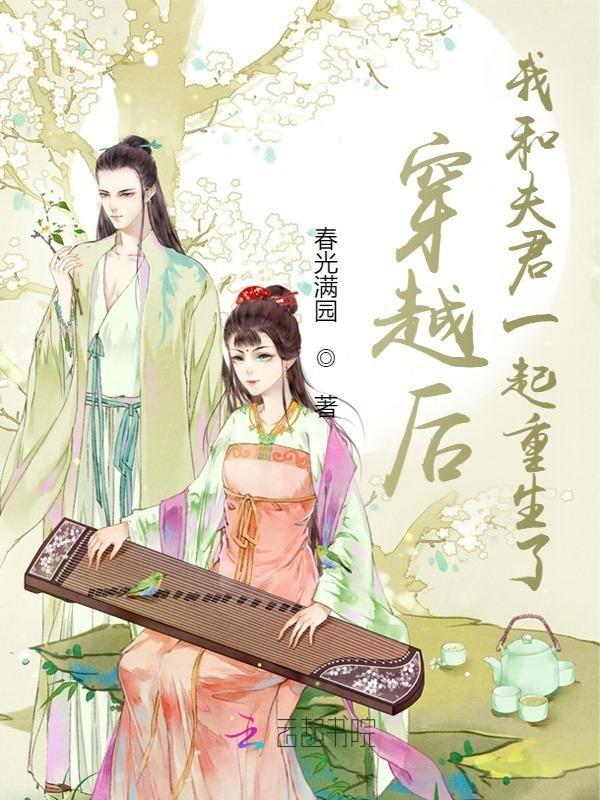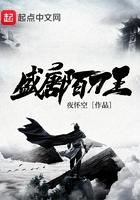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外科教父 > 1253章 赤子之心(第1页)
1253章 赤子之心(第1页)
南都医大老旧的家属区,项老院士的书斋。
夜深人静,八十三岁的项老院士却毫无睡意。书房里灯光昏黄,空气中弥漫着旧书和墨汁混合的独特气味。他颤巍巍地拿着放大镜,正逐字逐句阅读着一份关于“破壁”计划的材料。
当读到杨平团队因进口特种酶断供,不得不采用“土法”表达纯化,研究人员双手被培养基染得斑驳的细节时,秦院士的手猛地一颤,放大镜险些脱手。他闭上双眼,深吸一口气,仿佛要将那久远岁月里的苦涩与坚韧重新吸入
肺腑。
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,那些被尘封的艰苦,那些共同奋斗的身影,那种为国家需要而献身的纯粹激情,如同潮水般涌上心头,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他猛地睁开眼,浑浊的眼底迸发出锐利如青年般的光芒。他放下放大镜,抓起书桌上的手机,手指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,但他拨号的动作却异常坚定。
电话接通,那头传来他最得意的门生,如今已是国内顶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??李明达教授恭敬的声音:“老师,这么晚了,您还没休息?”
“明达!”秦院士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急切,甚至有一丝罕见的严厉,“那个”破壁’计划,前因后果,你都清楚了吗?”
“老师,我知道了,我们正在密切关注,考虑如何配合……………”
“光是关注和配合还不够!”秦院士打断他,语气加重,如同重锤敲击,“这是关乎国脉民命的大事!我们这些老家伙,土埋到脖子了,冲不动一线了,但你们呢?你们正值当年,是国家科技事业的脊梁!我听说他们现在最缺
的,不是钱,不是设备,是能挑大梁,能打硬仗的顶尖人才!是既有扎实功底,又有破局勇气的青年才俊!”
他喘了口气,继续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:“你手下那个赵默,去年在《自然》上独立发表蛋白结构论文的那个小伙子,灵性十足!还有那个从斯坦福交流回来的李颖,搞计算生物学和AI辅助药物设计,思路非常前沿!都是
好苗子,是璞玉!你去做工作,务必说服他们,放下手头那些不痛不痒的课题,立刻加入到“破壁’计划中去!”
电话那头的李院长显然有些犹豫:“老师,我明白您的意思。只是。。。。。。赵默的博士论文正处在最关键的数据收尾阶段,李颖也刚申请到一项国家青年基金,而且。。。。。。国外几个顶尖实验室,比如哈佛的戴维森实验室、剑桥的LM
B,都给他们发了博士后offer,条件非常优厚。。。。。。这个时候让他们转向,会不会。。……………”
“优厚?国外给的再多,那也是锦上添花!是给别人做嫁衣!”项老院士的声音陡然提高,声音因为激动而颤抖,“回来参加“破壁”,是雪中送炭!是为我们争一口不受制于人的硬气!这意义能一样吗?!论文可以晚点毕业,
基金可以带过去,国外的offer推掉!告诉他们,这是我项望山的请求!是我这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,对他们唯一的请托!”
他的话语,承载着老一辈科学家的期望,遗憾与重托,沉重得让电话那头的李院长瞬间沉默。书房里只剩下项院士略显粗重的喘息声。
良久,电话里传来李明达低沉而坚定的回应:“老师,您别激动,我明白了。是我一时糊涂,忘了根本。您放心,我亲自去找他们谈。无论如何,我一定把赵默和李颖,送到‘破壁’计划最需要他们的岗位上!”
放下电话,项老院士仿佛耗尽了力气,缓缓靠在椅背上,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,眼中闪烁着欣慰与期待的光芒。
他又在心里盘算着电话该往哪里打,南都医大数字医学中心的小何已经是破壁计划的中流砥柱,校长苏青云更不用说,现在肯定在运筹帷幄之中,不用他再多说。
除了李明达,项老院士还有很多颇有成就的学生,目前身居重要岗位,有些还在国外顶级大学或实验室,想起国外,他想起张春泉,顿时心里隐隐作痛。
张春泉是他曾经给与最大心血与期望的学生,可是,可是。。。。。。
哎!项老院士心里涌上一般深沉的痛惜与难以言喻的难受。
美国马萨诸塞州,剑桥市。
麻省理工学院,白头生物实验室在全球享有盛誉,年仅二十八岁的陈潇刚刚在这里博士毕业。
他怔怔地站在落地窗前,俯瞰着查尔斯河上星星点点的灯火与穿梭的帆影。窗外是剑桥市的繁华与宁静,窗内,他的内心却正经历着一场惊涛骇浪。
他刚刚结束与导师??诺贝尔奖得主戴维森教授的长谈。维森教授极力挽留陈潇在实验室担任独立PI首席研究员的邀请。
同时,他也收到一家顶级生物科技公司开出的高达五十万美元年薪、外加丰厚股权的offer。
现在陈潇的手中,平板电脑的屏幕还亮着,上面显示着国内关于“破壁”计划的详细报道,以及他的母校老校长亲自发来的,情真意切的邮件。邮件里,老校长转达了项望山院士等老一辈科学家的殷切期望。
陈潇是近年来在基因编辑和核酸药物领域横空出世的华人新星。他在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,被业内誉为“开辟了新的可能性”,多家顶级期刊向他邀稿,无数橄榄枝从世界各地伸来。留在美国,他拥有世界顶级的科研平台、充
足的经费支持、以及一条清晰可见的,通往学术巅峰或财富自由的康庄大道。
但此刻,那些曾经让他心动不已的条件,在“破壁”这两个字面前,似乎都失去了色彩。他想起了几年前出国时,年迈的父亲在机场拍着他的肩膀,那句朴实无华的叮嘱:“潇潇,学成了,要记得回来。”他想起了在国内读研
时,实验室里那台因为精度不够而需要反复校准,导致他无数个夜晚无法安睡的旧仪器。
更想起了报道中,杨平教授在面对封锁时那句平静却石破天惊的话:“这不是我们一个课题组的战争。”
他曾经在一个学术会上见过杨平教授,那时他是远远的观望,并没有近距离接触。杨教授是他的偶像,是他心中的真正天才,那时他觉得自己的能力不够,无法做到与杨教授在专业领域顺畅沟通,所以只能远远地坐在最后一
排,他发誓一定努力,努力有一天能够和杨教授面对面讨论学术难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