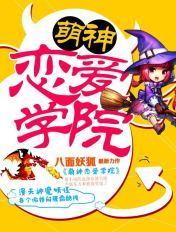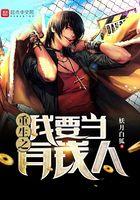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错练邪功,法天象地 > 第578章(第2页)
第578章(第2页)
而在角落的抽屉里,发现一本日记。扉页写着:“第七轮矫正日志??患者代号‘松七’”。
翻开第一页,字迹颤抖:
>“今天我又说了谎。我说我杀了兄弟,因为我嫉妒他升职。其实我没有。但我们必须这样说,否则药就不会停。这里的医生说,只要我们承认十种不同的罪行,就能获得自由。可我已经说了二十种,他们还是不放我走。
>昨晚我梦见女儿,她站在阳光下叫我爸爸。可当我伸手去抱她,她的脸变成了镜子,里面只有我自己在哭。
>我开始怀疑,到底哪个才是真的我?”
唐绾绾合上日记,泪水滑落。
就在这时,整座大厅突然震动。那台言语校准仪的指针疯狂旋转,发出刺耳鸣响。紧接着,四面八方的小室门同时开启,一个个身影缓缓走出??皆是衣衫褴褛、面容枯槁之人,眼神空洞,口中机械重复:“我有罪……我需矫正……请给我药……”
“他们是试验品!”老医师惊呼,“长期服用记忆抑制剂导致人格解体!他们的自我认知已经被彻底打碎!”
唐绾绾强忍悲痛,走上讲台,高声喊道:“你们没有罪!你们是英雄!你们记得的一切,都是真的!”
人群停滞片刻,随即爆发出混乱的嘶吼。有人扑向镜子砸碎它,有人抱住头蹲地哀嚎,也有人怔怔望着她,眼中闪过一丝微弱的光。
小满冲上前,举起那枚青光石片,大声道:“看!这是你们的朋友送出的信号!他们没放弃你们!外面的世界正在听!”
奇迹般地,一名白发老人踉跄上前,盯着石片良久,忽然老泪纵横:“这……这是我刻的!我在碑林做苦工时偷偷磨的!我以为没人会捡到……我以为我们都死了……”
唐绾绾跪在他面前,握住他的手:“您没死。您的名字是?”
老人嘴唇哆嗦:“赵……赵守义。北岭二营炊事兵。我没杀过人,也没逃。我只是……一直给战友们做饭,直到最后一顿炸酱面。”
人群中响起抽泣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报出自己的名字、部队、职务。有人记不清了,就在地上画军徽;有人失语了,就用手比划动作。唐绾绾带领团队一一登记,每一笔都郑重其事,如同为亡灵超度。
三天后,第一批幸存者被接出地底,送往临时疗养所。消息一经传出,举国震动。更多线索如雪片般飞来:南方某湖底发现沉没的“静默塔”,塔内囚禁着百余名因言论获罪的知识分子;东北边境一处废弃广播站,每日凌晨自动播放一段童声朗诵:“我爱你祖国,所以我必须忘记你”;甚至有前宫廷乐师作证,皇帝年轻时曾被迫参与一场“声音净化仪式”,将自己的真实情感录成唱片,当场焚毁。
朝廷再度陷入动荡。虽已撤销对唐绾绾的指控,但朝中保守派势力暗中串联,指责她“掀起旧怨,动摇国本”。更有御史联名上奏,称“真相辑录馆实为叛逆巢穴”,请求查封。
然而这一次,民间反应空前激烈。各地书院学子自发组织“朗读会”,在街头公开宣读幸存者证词;商贾阶层捐资建立流动倾听屋,专为底层百姓提供匿名倾诉渠道;甚至连一向冷漠的贵族女子也开始秘密结社,分享被家族掩盖的婚姻暴力与精神压迫。
一场静默的觉醒正在蔓延。
某夜,唐绾绾独坐馆中整理档案,忽觉心口一震。抬头望去,窗外星空璀璨,而心钟树的方向,第十七片叶子正缓缓舒展,新诗浮现:
>“当你终于敢说出‘我不是凶手’
>那些真正流过的血
>才有了名字。”
她含泪微笑,提笔在案卷末尾写下:
>“今日共接收证词一百零三条,找回姓名八十九人,确认存活十二人。
>地下网络尚未完全破解,回音谷位置仍未确定,但希望已在生长。
>我坚信:言语的力量不在宏大的宣言,而在每一个微弱却真实的‘我在这里’。”
翌日,阿弦带来惊人发现??通过对言语校准仪的拆解,他们在底部铭文中找到一组坐标,指向东海某孤岛。查阅古籍后确认,该地曾为皇家“遗音阁”所在地,专用于封存“不宜流传之声”,包括先帝临终忏悔、皇室政变录音、以及……一段关于开国元勋集体自杀的秘闻。
“也许,”阿弦说,“真正的起点,不在北岭,也不在西州,而在那个被海浪吞噬的岛上。”
唐绾绾望向远方,海风似乎已吹拂至耳边。
她知道,这场风暴才刚刚开始。但她不再恐惧。因为她终于明白,《倾听者十诫》真正的意义并非教导人们如何说话,而是告诉这个世界:**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等待,哪怕它迟到了几十年,哪怕它来自深渊之下,哪怕它只是轻轻一声叹息。**
黄昏时分,一个小女孩来到馆门前,怯生生递上一封信。信封上无署名,只画着一朵松花。
唐绾绾拆开,里面是一张稚嫩笔迹的纸条:
>“妈妈昨晚哭了。她说爸爸十年前就被抓走了,因为他写了首诗,说战争很痛。
>我不知道诗是什么,但我想让它回家。
>请问,诗也能被原谅吗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