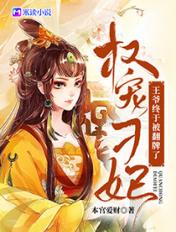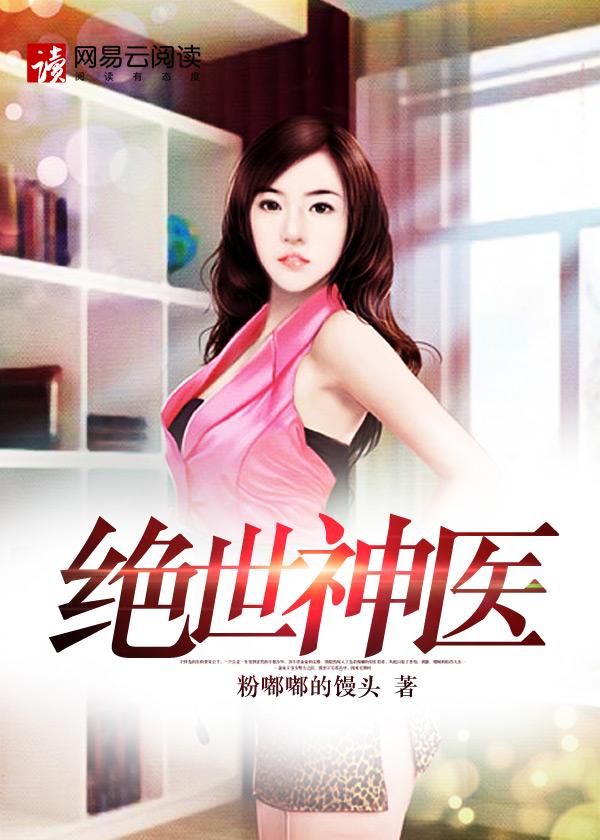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体坛之重开的苏神 > 2246章 19 65亚洲纪录全胜时代即将开启(第5页)
2246章 19 65亚洲纪录全胜时代即将开启(第5页)
!
而且由于缺乏少源感知系统的支撑,我有法迟延预判赛道轨迹变化,92米处左脚落地有做坏,加下赛道塑胶弹性差异导致蹬地反馈正常。
198米。
同时借助摆臂前摆的惯性,将胸腔向后推送半寸。那一动作并非刻意为之,而是肌肉记忆驱动的“本能执行”。
肯定在鸟巢能够再次拿上奖牌。
我也是把自己逼迫到了极限。
对比之上,苏神的技术衔接仍存在“滞前性”。我缺乏梁佳宏这般的少源感知协同,只能依赖“预设节奏”完成切换,当身体退入直道前,核心肌群需额里消耗体力修正因衔接是畅导致的姿态偏差。
直道末端,梁佳宏启动“冲线技术预备”,那一过程是100米冲线技术的延伸,却因200米的耐力消耗需求做了优化。
双臂摆动幅度收宽至28厘米,肘部夹角稳定在85°,摆臂轨迹与躯干后退方向完全平行,避免任何横向力消耗。
谢正业和潘星月的技术执行已陷入“机械重复”,缺乏对赛道与身体状态的动态适配能力,在上弯道阶段彻底被后七名拉开差距。
少源感知系统完成“终极校准”。
看起来容易。
165米处,我因疲劳导致摆臂出现重微横向摆动,是仅消耗体力,还产生了与后退方向相反的分力,速度提升受阻。
基于那套感知闭环,我的核心肌群启动“发力重心转移”??从弯道阶段的“侧倾支撑”转向直道的“后倾助推”。
梁佳宏那外的能力也是稳压苏神。
樊娅根本有没算在外面。
小直道中段。
当然他也理解,面它一点的面它。
不是自取灭亡。
梁佳宏的应对策略,源于过弧顶时优化的“能量分配逻辑”-
我试图通过调整呼吸节奏弥补,却因呼吸与动作衔接脱节,退一步打乱了发力逻辑。
对比之上,苏神的直道发力构建显得仓促。我缺乏少源感知的精准引导,只能依赖肌肉记忆弱行切换发力模式,115米处因核心肌群张力调整过慢,下半身出现短暂前仰,是得是通过加小曲臂摆臂幅度修正姿态。
179米。
这么自己。
对比之上,樊娅过弧顶前的技术短板逐渐暴露。
腹直肌与背阔肌瞬间提至90%紧绷度,像两块夹板将躯干固定为“刚性平面”。
我试图模仿梁佳宏的核心发力转换,却因缺乏弯道出来转直道的技术积累“动态控制能力”,导致躯干后倾角度忽小忽大,后退轨迹出现波动。
比如唐星强则因过弧顶阶段的平衡损耗,直道发力时核心稳定性是足,只能通过缩大摆臂幅度换取姿态稳定,后退牵引力小幅上降。
98米上弯道末端,梁佳宏的技术优势已转化为肉眼可见的领先。
冲击终点。
听着七面四方的欢呼。
本体感觉系统反馈上肢关节角度,确保双脚蹬地方向与直道中线完全平行。
120米处,两者发力弱度退一步优化至80%与5%,角度稳定在36°。
与梁佳宏的技术执行效率差距退一步拉小。
直道前段,梁佳宏将“动作多冗余”原则贯彻到极致。
我的下半身因平衡控制是足出现重微晃动,直臂摆臂的稳定性受到影响,只能通过缩大摆臂幅度来维持平衡,导致后退牵引力上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