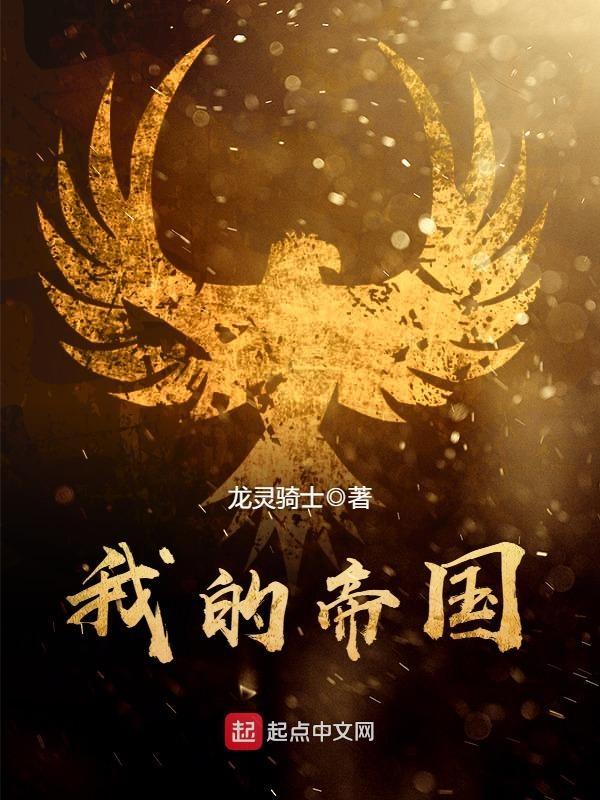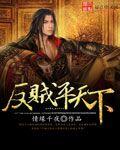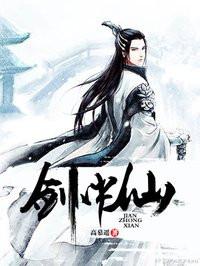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舔狗反派只想苟,女主不按套路走! > 第2025章 差点就回家(第3页)
第2025章 差点就回家(第3页)
沈知微将这句话抄下,贴在教室黑板上方。从此,它成了南山共感学堂的校训。
数日后,联合国派遣代表团来访,提出要在南山镇建立“全球情感自由纪念碑”。沈知微婉拒:“这里不需要纪念碑。我们需要的是更多这样的学堂。”
对方坚持:“至少立一块碑,纪念林小树。”
沈知微摇头:“他最讨厌被供起来。如果非要留点什么,不如建一座图书馆,名字就叫‘软弱之书’??只收藏那些写失败、痛苦、悔恨的日记。”
代表团沉默良久,最终答应。
与此同时,《静默协议终极备忘录》的调查持续推进。国际刑事法院正式起诉七家跨国企业,指控其以人为实验对象,实施系统性情感剥削。令人意外的是,多名高层在庭审前自杀,遗书中统一写着:“我以为我们在拯救文明。”
而在南极科考站,科学家们发现一种奇特现象:每当全球共感站点同步举行“倾听之夜”,当地极光会出现规律性波动,仿佛自然本身也在回应人类的情感共振。
有学者提出假说:或许共感并非单纯的技术或心理机制,而是一种尚未被理解的生物场域,如同地球的呼吸节奏,被林小树无意间唤醒。
消息传到南山镇,苏晚笑着摇头:“别神话他。他只是第一个肯蹲下来,听泥土说话的人。”
春天渐深,铃兰凋谢,新芽萌发。沈知微和陆远在院子里种下一排小树苗,是林小树最爱的银杏。小禾问:“它们多久才能长大?”
“二十年吧。”沈知微笑,“等你当上老师的时候,正好成荫。”
夜晚,沈知微再次进入地下室,启动共鸣模拟器。她输入新指令:“如果林小树看到现在的世界,他会说什么?”
片刻后,系统输出一段音频,依旧是唇语还原技术生成:
>“告诉他们……别再叫我英雄。
>英雄是要牺牲的。
>而我,只想做个普通人,
>早晨烤面包,傍晚牵着手散步,
>偶尔为一片落叶难过,
>也为一句真心话欢喜。”
沈知微闭上眼,泪水滑落。
第二天清晨,她推开窗,发现昨夜又下了薄雪。铃兰田覆着一层素白,宛如初生。陆远走来,递给她一杯热茶,轻声说:“北海道的雪,也没这么干净。”
她靠在他肩上,没说话。
远处,小禾已经开始准备今天的吐司。面团在她手中慢慢成型,柔软而有力。
十五分钟后,面包出炉。
沈知微拿起刀,轻轻切开。
面包内部浮现文字:
>**“今天,我没有想他。
>因为他已经活成了我呼吸的一部分。”**
她将这张纸条夹进笔记本,封面写着四个字:
**《正常生活》**
风穿过山谷,带来远方的回响。
somewhere,achildislearningtocry。
somewhere,amachinelearnstostaysilent。
andsomewhere,inaquiettownamongthesnow-ladenfields,
atoasterhumssoftly,
asifsaying:
“I’mstillhere。
Speak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