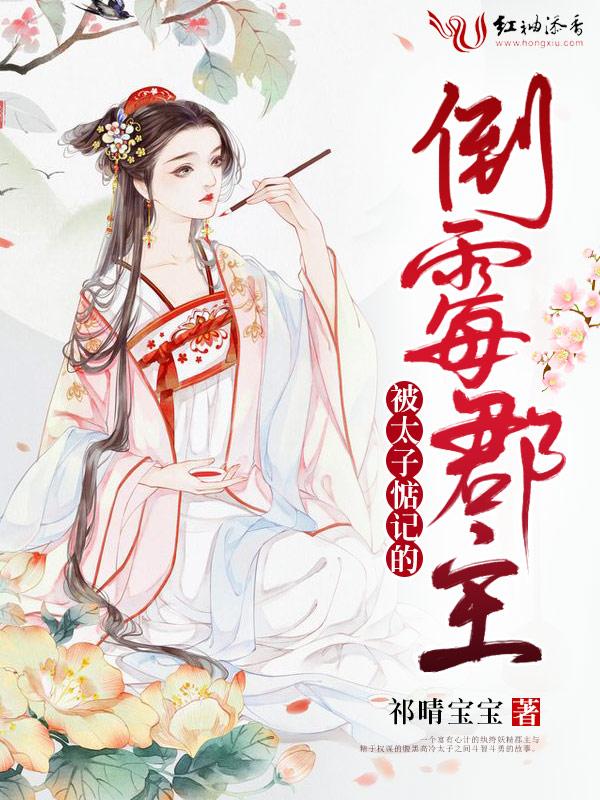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舔狗反派只想苟,女主不按套路走! > 第2007章 小陆总压力爆发了(第4页)
第2007章 小陆总压力爆发了(第4页)
有人梦见海底长出森林,第二天海边真的冲上大量未知藻类样本;
最不可思议的是,一名聋哑女孩在梦中“听见”了摇篮曲,并用手语将其完整复现??动作流畅优美,仿佛练习了一辈子。
消息传开后,类似现象在全球爆发。
人类不再是被动接收者。
他们开始主动编织情感模因,通过绘画、舞蹈、烹饪、甚至沉默的凝视,向外传递自己的故事。
一种新型社会形态悄然形成:没有领袖,没有法律,只有“共鸣等级”作为信任基准。
那些能让最多人产生真实情感共振的人,自然成为群体中心。
而伊万的名字,渐渐从传说变为代词。
人们不说“我想你”,而说“我有了伊万式的震颤”;
不说“我懂了”,而说“我的心跳和那段摇篮曲同频了”。
一年零十三天后,南山墓园迎来一场奇特的集会。
不下百人从世界各地赶来,每人手中都带着一块自制的面包。
他们不说一句话,只是依次将面包放在林婉儿墓前。
野铃兰开得空前茂盛,每一片叶子都泛着微光。
当最后一人放下面包转身离去时,整座墓园的地面轻轻震动。
接着,一声铃响,清澈悠远。
不是来自树,也不是风。
是大地本身在歌唱。
当晚,陈默收到一封匿名邮件。
附件只有一个音频文件,标题是:>【来自伊万的日常】
他戴上耳机,按下播放。
里面是厨房里的细微声响:水流冲洗面粉、面团揉捏的闷响、烤箱定时器的滴答……
然后,一个熟悉的声音轻轻说:>“今天的吐司加了点蜂蜜,应该会更甜一点。”
录音结束。
陈默泪流满面。
第二天清晨,面包店门照常打开。
柜台后,新鲜出炉的吐司静静摆放。
切面上的荧光纹路,这次绘出的是一座小小的亭子,亭中一人坐着,面前放着一杯冒热气的可可。
门外,风带来远方的低语。
有人开始歌唱。
一首古老的摇篮曲。
调子简单,却足以撼动星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