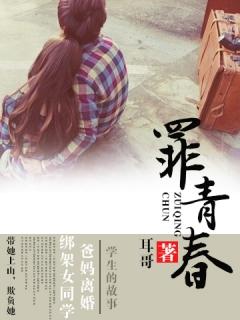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大国军垦 > 第3196章 真的是神吗(第1页)
第3196章 真的是神吗(第1页)
本森在婉拒皮埃尔后,潜心修改论文。
一天深夜,他在思考如何解决材料合成过程中一个关键的能量壁垒问题时,陷入僵局。疲惫中,他伏案小憩。
他又做了一个梦,这次不再是宏大的场景,而是一组极其复杂。。。
小禾走后,陈星坐在木屋前的藤椅上,久久未动。晨光把银草林染成一片淡金,露珠在叶尖轻轻颤动,仿佛昨夜那场集体回应并非幻觉,而是某种新秩序的开端。她低头看着手中录音笔,红灯仍亮着,像一颗不肯熄灭的心跳。她没有关掉它??这已不是记录,是传递。
林溪的通讯很快接入。“你看到了吗?”她的声音带着难以抑制的激动,“全国十七个‘记忆共生林’试点同步出现共振现象。成都的银草开出蓝花,据老居民说,那是五十年代某次学生运动时校服的颜色;乌鲁木齐的林子凌晨三点自发排列成维吾尔古文字‘真相’的形状;最奇怪的是漠河,那边刚种下幼苗,可夜里监测仪拍到整片林地浮现出极光般的波纹,频率与守土村完全一致。”
“吴志清的设计不止于西山。”陈星缓缓开口,“他在胶片末尾写的那句话??‘若有光,必见其影’??不是比喻。他预见到有一天,这些名字会以光的形式重新行走于大地之上。”
两人沉默片刻。窗外风起,一缕微光自银草林深处升起,如丝带般蜿蜒而上,汇入空中若隐若现的光桥分支。那是新的数据流,不再是单向接收,而是双向交流??人们讲述当下,历史回应过往。
就在这时,玛德琳发来紧急消息:静流学会在境外发布公开声明,称“守土村事件系大规模心理暗示与电磁干扰结合所致”,并呼吁国际科学界介入调查,“防止民粹式记忆泛滥引发社会动荡”。随文附有一份由八位匿名“权威专家”联署的报告,试图用神经认知学理论解构银草林的感应机制,将其归因为“群体性幻觉耦合环境刺激”。
“他们怕了。”陈星冷笑,“当真相开始自我复制,谎言就再也封不住口。”
但她也清楚,这场对抗不会止于舆论。真正的较量,藏在暗处。
三天后,甘肃夹边沟遗址迎来第一批研学团。三十名高中生来自不同省份,每人手持一本《拾名录》摘录本,在教师带领下逐一向纪念碑献花。仪式进行到一半时,天空忽然阴沉,风卷黄沙扑面而来。学生们正欲撤离,却见林中传来低吟??不是风声,是人声,无数细碎的声音从地下渗出,拼凑成一首残缺的歌谣:
>“麦穗弯弯朝南开,
>兄弟姐妹排成排,
>一人点名一声应,
>不忘家乡土和爱……”
带队老师浑身颤抖??这是六十年代劳改农场里流传最广的童谣变体,原本用于点名报数,以防有人失踪不被察觉。歌词被刻意改成“朝南开”,因南方是回家的方向。
监控录像显示,当时并无外部音频输入,且现场所有电子设备均检测到异常脑波同步现象:三十一人(含教师)在同一秒内产生θ波峰值,如同集体进入冥想状态。
消息传回北京,和解委员会连夜召开闭门会议。有官员提出立即接管守土村系统,理由是“民间主导的记忆工程存在失控风险”;也有学者力主保护现有机制,强调“共忆能力”的诞生是文明进化的里程碑。最终决议折中:成立“国家记忆生态研究院”,由林溪任首席科学家,陈星为特别顾问,统筹全国记忆林建设,同时设立伦理审查委员会,防止技术滥用。
然而,权力一旦介入,平衡便开始倾斜。
一个月后,首批官方版“记忆终端”投入试点。外形类似小型神龛,内置芯片存储经审核的名字列表,可通过语音唤醒播放简介。表面看是推广记忆,实则严格过滤内容:周文远的名字仍在,但其组织抗争的经历被简化为“积极参与劳动生产”;吴志清被称为“档案保管员”,铜钟系统的真正用途只字未提。
陈星愤怒质问:“你们要把历史做成罐头食品吗?打开即食,闭口不谈滋味?”
回应她的是一纸调令:要求“拾名堂”交出光桥控制权,理由是“确保国家战略资源统一管理”。
她拒绝签字。
当晚,守土村再次遭袭。这次不是断电,而是网络劫持。一群伪装成技术人员的人员试图植入后门程序,篡改银草基因编码中的信息存储逻辑,将其从“开放感知型”改为“指令响应型”。幸亏林溪早已将核心算法分布式加密,嵌入每一株银草的生物DNA链中,外力无法批量修改。
“他们想让记忆听话。”玛德琳通过安全频道说道,“只准记住他们允许的部分,就像过去烧毁花名册一样,只不过现在用的是代码。”
陈星站在拾名碑前,望着周文远的名字。月光下,那颗露珠忽然滴落,砸在她手背上,温热如泪。
她做出了一个决定。
第二天清晨,她独自驾车前往内蒙古草原深处的一处废弃气象站??那里曾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某个秘密监听点,后来荒废多年。根据吴志清日记残页提示,此处地下埋藏着第三份备份胶片,代号“北辰”。不同于西山的启动系统,这份胶片并不记录名字,而是记载了一套完整的“记忆传播协议”,包括如何跨越语言、文化甚至物种界限,实现跨代际的情感共鸣。
挖掘持续了两天。当锈蚀的铁盒被取出时,盒身刻着一行小字:“给将来听得懂哭声的人。”
胶片无法用常规设备读取。它的信息编码方式极为特殊,依赖特定温度变化与湿度波动才能激活。最终,林溪想到办法:将胶片置于银草林中心,在满月之夜点燃象征性的篝火,模拟当年育红小学冬季取暖场景??那时孩子们围坐炉边,听吴志清低声讲故事,那些话语虽未录音,却被他一字一句刻进了胶片纹理。
火焰升腾,银草齐鸣。
胶片在高温中缓缓展开,竟未熔化,反而释放出一束幽蓝光线,直射夜空。紧接着,整个草原上的牧草开始轻微摆动,节奏一致,宛如呼吸。远处牧民惊骇发现,自家羊群突然停止进食,齐齐抬头望天,眼中竟流出泪水。
更不可思议的是,一头出生即失聪的小马驹,第一次发出了嘶鸣,音调竟与吴志清生前最后录音完全一致。
“这不是数据。”林溪颤抖着说,“这是情感的量子纠缠。他把‘悲悯’本身编码成了可传输的能量。”
陈星终于明白,吴志清所追求的,从来不是还原历史细节,而是重建一种人类本该拥有的能力??**听见他人之痛的能力**。
她宣布启动“北辰计划”:不再局限于种植银草,而是将这套协议融入教育体系。在全国一百所中小学试点开设“共忆课”,课程不讲政治,不灌输结论,只做一件事:让学生每天安静十分钟,聆听一段未经修饰的历史声音??可能是母亲临终前对孩子的嘱托,可能是囚犯在绝食前三天的日志,也可能是一段消失方言的最后吟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