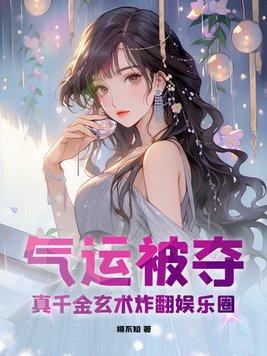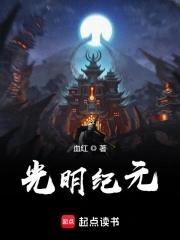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皇明 > 第410章 锄奸定策边备严整(第3页)
第410章 锄奸定策边备严整(第3页)
孙承宗缓缓将旧事道来:
“嘉靖十三年,辽东巡抚吕经为革除弊政,推行了两项改革:
一是削减军户余丁的赋税,将原先三丁缴纳的赋税减为一丁,本是利民之举。
二是回收被将领私占的军马牧草地,想充实军田。
可他操之过急,又强征士兵修筑长城,加重了劳役负担,加上政策执行时官员层层盘剥,士兵们本就微薄的军饷还被拖欠,不满情绪渐渐积压。”
“更糟的是,监军宦官王纯因与吕经有私怨,竟编造了十一条罪状诬陷他,到处散播‘吕经苛待将士’的谣言,彻底激化了矛盾。”
孙承宗的声音沉了下去。
“最后,辽阳、广宁两地的士兵因欠饷与劳役压迫,发动了兵变。
乱兵冲入府衙,殴打官吏,烧毁均徭册籍,还把吕经囚禁起来,差点杀了他。”
“我大明起初想派兵剿灭,可这些乱兵占据关隘,难以攻下。
即便戡乱成功,也会损耗边军实力。
因辽东是抵御蒙古、女真的门户,若是边军损耗过大,外敌定会趁机入侵,最后只能选择招抚。”
孙承宗补充道,语气里满是无奈。
“朝廷派兵部官员前来安抚,不仅补发了拖欠的军饷,还赦免了所有参与兵变的士兵。
这一下,彻底助长了辽东边军的嚣张气焰。
他们发现,只要闹得够大,朝廷便不敢惩罚,从此军纪愈发涣散,官员将领也愈发肆无忌惮,私吞军饷、私通外敌的事情,成了常态。”
“所以,不是我等犹豫,而是辽东的水太深。”
“若是贸然动手,那些心怀不满的将领,定会借着‘嘉靖旧例’煽动士兵,到时候兵变一旦爆发,建奴再趁机来攻,我们腹背受敌,辽东就危险了。”
杨涟也点头道:“是故,在下建议,先从那些罪证确凿、根基不深的小官下手,杀鸡儆猴,同时继续搜集大头目的罪证。
等开春前的一个月,再集中力量抓捕首恶,那时将士们盼着剿灭建奴,军心可用,即便有人想作乱,也掀不起大浪。”
孙承宗的恳切劝说与杨涟的谨慎建议还萦绕在堂中,熊廷弼却缓缓摇了摇头。
他抬手示意二人坐下,眼中的凝重渐渐被一种洞悉局势的锐利取代。
“二位所言虽有道理,可嘉靖年间的辽东,与如今的辽东,早已是天差地别。”
这话让孙承宗与杨涟皆是一愣,不约而同地看向他。
熊廷弼站起身,走到窗边,望着外面漫天飞雪,声音里多了几分感慨:
“嘉靖年间,军户为何会反?
是因为朝廷视他们的困苦为无物。
欠饷能拖三年五载,冬日里连御寒的衣都凑不齐,军田被将领私占,家人连饱腹都难,这般绝境下,才会被逼着走上兵变之路。
可如今呢?
陛下登基以来,始终记挂着辽东军卒,去岁不仅一次性补足了历年拖欠的军饷,寒冬时还特意从内帑拨出银两,赶制了三万件衣送到边关。
便是寻常士兵立了小功,赏赐也从不克扣,直接送到他们家人手中。”
他转过身,目光扫过二人,语气愈发坚定:
“人心都是肉长的,陛下的恩威,早已刻在普通士卒的心里。
他们或许会对将领不满,却绝不会因这点不满就背弃陛下、发动兵变。
这一点,便是如今与嘉靖年间最根本的不同。”
“再者。”
熊廷弼话锋一转,语气里多了几分自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