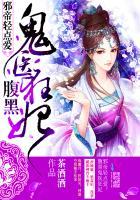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皇明 > 第400章 藩心归服天威远播(第2页)
第400章 藩心归服天威远播(第2页)
朱由校低声叹息。
他绝不能让历史重演。
朱由校怀中抱着已有身孕的皇后张嫣,眼神却是格外的深邃。
若未来后宫诞下皇子皇女,教育模式必须彻底革新。
他心中已有腹稿。
保留洪武时期的“文武并重”与中期的“严格考核”。
皇子八岁出阁,经史、骑射仍是基础,每日课业不可懈怠。
摒弃文官对教育的绝对掌控,讲师除了名儒,还需加入退役将领(授兵戈之术)、地方清官(讲民生疾苦)、皇商官员太监(论经济利弊)。
废除“只重典籍不重实操”的弊端,皇子十岁起需入阁观政,十五岁后要下地方巡查,去灾区看流民、去边关见士兵,亲身感受“大明江山”,绝非仅是紫禁城的红墙黄瓦。
新增“帝王心术”(教权衡之术、辨忠奸之法)、“天下视野”(讲海外诸国、草原部落)、“基层经验”(学农桑、知赋税)。
他要培养的,是“知民间疾苦、懂天下格局、有决断魄力”的帝王,而非困于文牍、受制于文官的“傀儡”。
可朱由校也清楚,这场革新注定阻力重重。
太子乃国本,教育模式的改变,本质是对“文官主导的教育权”的挑战。
那些早已习惯规训帝王的朝臣,定会以“祖制不可改”“国本不可动”为由激烈反对,甚至可能引发新的“国本之争”。
好在。
如今徽媖尚幼,皇子未生,他还有数年时间。
这数年时间里,他要平定辽东、整顿江南税改、清除朝堂蛀虫,将大明的权柄牢牢握在手中。
待他根基稳固、威望足以震慑朝野时,再推教育革新,那时,纵有反对之声,也无人敢真正阻挠。
丰台大营外,来了数千骑兵。
正是从辽东而来的布和等一行人。
布和特意勒住马,看向身后那些随他一同来京的辽东军卒一个个涌入丰台大营。
这些兵卒,有戚家军,有白杆兵,有狼兵
都是精锐中的精锐,虽然每支只来了三百人,但一看就不好招惹。
除了这些劲卒之外,还有伤兵。
断了左臂的浙兵,腿上留着箭伤的川兵,被炸得满脸狰狞的狼兵
这些兵卒虽然各个带伤,但精气神却似一把锋芒毕露的宝剑一般,让人不敢直视,也不忍直视。
与明军分别,他和被押送过来的林丹汗、莽古尔泰等很快进入京城。
爆竹声中一岁除。
除夕的北京城都很是热闹。
这热闹,与布和一路从辽东而来的苦寒景象,有着天壤之别。
他裹着厚厚的蒙古皮袍,骑在马上,望着眼前的繁华,忍不住喃喃赞叹:
“这就是大明国的京城吗?当真是天朝上国啊!”
布和进入北京城,就像是个乡巴佬一般,看什么都稀奇。
在这个时候,他忽然明白为何大明皇帝要让那些伤兵到京城来了。
听说明国元日大典会阅兵,待元旦大典阅兵时,这些带着战火痕迹的士兵,定会让京城的群臣与百姓明白:
眼前的纸醉金迷、岁月静好,是用多少士兵的血肉换来的。
你的岁月静好不是凭空来的,而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。
他不禁想起草原的冬日,牧民们为了一口粮食挣扎,而大明的百姓却能在除夕这般肆意欢闹,心底竟泛起一丝复杂的滋味。
在布和台吉复杂的心绪之中,队伍抵达会同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