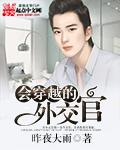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皇明 > 第380章 税滞江南谁家天下(第4页)
第380章 税滞江南谁家天下(第4页)
若是他无故打破周期,定会被言官们扣上“破坏祖制”“专断独行”的帽子,到时候不仅内阁会反对,连宗室勋贵都可能出来说情,反而激化矛盾,连眼下的新政都可能受牵连。
更何况,提前京察太容易被解读为“皇帝不信任现有官僚系统”。
自他登基推行新政、整顿边军以来,文官们对新政的非议就没断过,若是再动京察,怕是会引来更大的反弹。
辽东战事还靠着文官们在后方筹粮,他不能把所有文官都推到对立面。
“朕不搞大察,却也不会放任不管。”
“先把这话放出去,让江南的官员们知道,朕盯着税收这事呢。真要是到了年底还缴不上来,或是查出来有猫腻,到时候可就不是‘京察’那么简单了。”
这是他退而求其次的法子。
不搞全面京察,避免与文官集团正面冲突,却借着“派钦差小察”的风声,先震慑住那些敢借税收做文章的官员。
既保留了皇帝的威严,又给了文官们台阶,算是眼下最稳妥的策略。
三位大臣闻言,面色各异:
方从哲眉头微蹙,他既担心这风声震慑力不足,又怕真要派钦差时,会引发江南官场的动荡,一时拿不定主意。
李汝华则捻着胡须,神色平静,似乎在琢磨这风声该如何传达到地方,才能既不失威严,又不激化矛盾。
唯有李长庚,紧绷的肩膀悄悄放松了些。
他最怕皇帝当场发怒,追责户部办事不力,如今皇帝不仅没雷霆大怒,反而只让“多上心”,显然是暂时没打算追究他的责任,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半截。
朱由校看着三人的神色,心中也有些烦闷。
税收的难题、江南的阻力、文官的牵制,像一团乱麻,让他实在心累。
这皇帝,当真没那么好当啊!
他摆了摆手,声音里带着几分疲惫:“税收之事,你们多盯着些,有消息随时禀报。都下去吧。”
“遵命!”
李汝华与李长庚两人当即离去。
然而。
内阁首辅方从哲却没有随之退去,他依旧端坐在小凳上。
朱由校见这老小子不走,知道他肯定是有话要说的。
“元辅,还有什么要教朕的?”
片刻的沉默后,方从哲缓缓起身,整理了一下衣袍,对着朱由校躬身行了一礼,语气带着几分难以掩饰的疲惫,却依旧保持着老臣的恭敬:
“老臣不敢言教。”
方从哲可不敢把面前这个将他随意玩弄的皇帝当做学生。
缓了一口气,他继续说道:
“陛下,江南税收迟滞,新政推行受阻,皆因老臣身为内阁首辅,却未能调和群臣、督办事务,实乃无能之过。
恳请陛下准许老臣致仕,另择贤能接替首辅之位,以安朝局。”
这话出口时,方从哲的声音微微发颤。
他并非真心想退。
自万历年间入阁,历经三朝,权力的滋味,让他沉迷。
如果能当首辅,他愿意一直当下去。
可新政以来的处境,实在让他难以为继。
皇帝信任他,将新政的统筹之权交给他,可手底下的官员却对他阳奉阴违:
推行番薯种植时,地方官敷衍塞责,把劣种发给农户;整顿边军时,京官们又联名上书,说他“苛待将士”。
前阵子陛下纳蒙古女子入宫,御史们弹劾的奏疏堆了半案,却没人敢直接指责皇帝,反而把“未能规劝陛下”的罪名扣在他这个首辅头上。
如今连江南税收都出了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