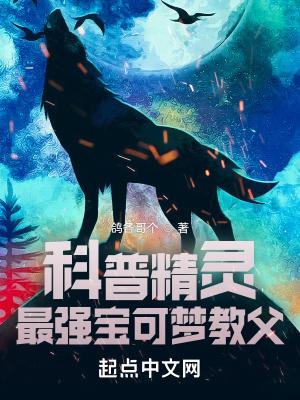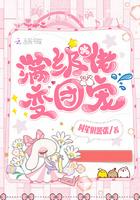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大唐:刑部之主,不科学破案 > 第140章 发现卷宗里的问题(第3页)
第140章 发现卷宗里的问题(第3页)
甚至因为杨文干曾救过他的命,是他的恩人,为了报恩,还暗中帮助杨文干。
冯木那段时间的几次怪异的行踪,就是为了帮助杨文干谋逆。
冯木是杨文乾的同谋!
而杨文干已经被秦王平叛,秦王与朝廷,就是害死杨文乾的最大仇人。
所以—冯木完全有理由,为杨文干报仇,而报復朝廷与秦王。
偷盗餉银的动机,顿时被任兴找到。
任兴连忙將这个发现稟告三司上峰,三司立即派人以冯木为中心,进行调查。
最终发现,那批运输餉银的將士,有百余人,是冯木的嫡系,也是冯木主动要求,將他们调集过来的。
並且任兴还发现,冯木曾在运输餉银之前,秘密与这百余人见过面,这百余人在运输途中,也曾一起守过夜。
也就是说—。他们完全可以趁著其他將士睡觉的时候,將餉银偷偷搬走,然后换成石头。
动机有了,帮手有了——三司当即对冯木等人严刑拷问。
最终,终於有將士承受不住,招了,说就是冯木收买了他们,让他们偷走的餉银。
只是冯木却一直没有鬆口,哪怕手下將士已经招了,仍是嘴硬的说他没有偷盗餉银。
而被盗走的餉银去处,也只有冯木一人知晓,那些將士只是帮冯木运走,交给了一些穿著夜行衣的人,所以想要知道餉银的下落,必须撬开冯木的嘴。
但冯木骨头太硬了,在牢內几乎要被折磨死,都没有开口。
反而大骂朝廷,大骂李渊,说李渊眼瞎,看不出忠奸善恶,最后將李渊彻底惹恼。
李渊一怒之下,餉银也不要了,直接將冯木等所有参与的人,集体问斩。
餉银案就此结案。
可那丟失的二十万贯餉银,到现在,也没有找到。
餉银去了哪里,那些黑衣人是谁,冯木想用餉银做什么——隨著冯木的死去,再也无人知晓。
看著卷宗上的结案二字,刘树义轻轻摇了摇头。
如果是他来调查此案,不查明餉银最终的去处,他绝对不会让此案完结。
更別说,此案看似线索与证据充分,合情合理。
可实际上,在刘树义眼里,全是问题。
比如,冯木既然都已经决定要偷盗餉银,那就必然知晓朝廷可能会查到他。
他既然准备的那般充分,能神不知鬼不觉盗走餉银,岂会想不到牌位与信件,可能会导致他暴露?
即便他捨不得恩人杨文乾的信件与牌位,不愿將其销毁,也至少该將其藏到外面,待他恢復自由后,再將其取回。
岂会明知有人会怀疑自己,会来搜查,还將这能够让他暴露的铁证留在宅邸?
再比如,卷宗里说冯木的下属招了,说冯木收买了他们。
可冯木具体怎么收买的,卷宗里並没有提及。
是当时审讯的人没有在意这个微不足道的细节,还是说每个人说的都不同?
若是每个人说的都不同,是冯木如此有耐心,对百余人每个人都有专门的收买计划呢,还是说。。这些人是被严刑逼供,最终受不了折磨被迫认罪,因他们就没有被收买,所以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同呢?
刘树义不知当时的具体情况,不会隨便怀疑查案的三司同僚。
但身为三司刑狱体系的人,在书写卷宗时,就该方方面面都写的细致完整,如这种缺少收买细节的卷宗,在刘树义眼里,便与废纸没什么区別了。
若是刘树义负责的案子,他手下的人这样书写卷宗,他绝对会打回去让对方重写,若再写不好,直接严惩换人。
这不是能力问题,而是態度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