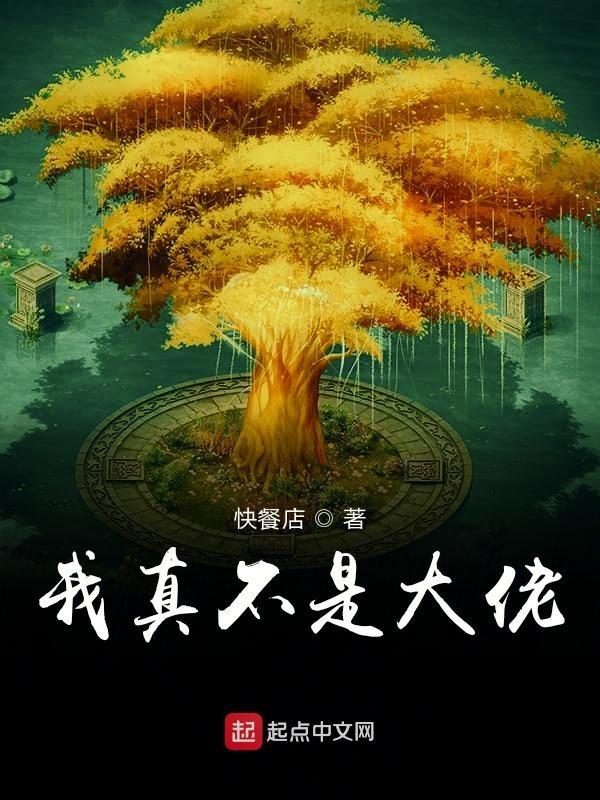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手把手教你读经典(全2册) > 宋学与蜀学(第1页)
宋学与蜀学(第1页)
宋学与蜀学
(一)二程与四川之关系
凡人的思想,除受时代影响之外,还要受地域的影响。孔子是鲁国人,故师法周公;管仲是齐国人,故师法太公;孟子是北方人,故推尊孔子;庄子是南方人,故推尊老子。其原因:(1)凡人生在一个地方,对于本地之事,耳濡目染,不知不觉,就成了拘墟之见。(2)因为生在此地,对于此地之名人,有精密的观察,能见到他的好处,故特别推崇他。此两者可说是一般人的通性,我写这篇文字,也莫有脱此种意味。
程明道的学说,融合儒释道三家而成。是顺应时代的趋势,已如前篇所说。至于地域关系,他生长于河南,地居天下之中,为宋朝建都之地,人文荟萃,是学术总汇的地方,故他的学说,能够融合各家之说,这层很像老子,老子为周之柱下史,地点也在河南,周天子定都于此,诸侯朝聘往来,是传播学说集中之点,故老子的学说,能够贯通众说。
独是程明道的学说,很受四川的影响。这一层少人注意,我们可以提出来讨论一下:
明道的父亲,在四川汉州做官,明道同其弟伊川曾随侍来川,伊川文集中,有《为太中(程子父)作试汉州学生策问》三首,《为家君请宇文中允典汉州学书》、《再书》及《蜀守记》等篇,都是在四川作的文字,其时四川儒释道三教很盛,二程在川濡染甚深,事实俱在,很可供我们的研究。
(二)四川之易学
《宋史·谯定传》载:“程颐之父珦,尝守广汉,颐与其兄颢皆随侍,游成都,见治蔑箍桶者,挟册,就视之,则易也,欲拟议致诘,而蔑者先曰:‘若尝学此乎?’因指‘未济男之穷’以发问,二程逊而问之,则曰‘三阳皆失位也。’兄弟涣然有所省,翌日再过之,则去矣。”伊川晚年注易,于未济卦,后载“三阳失位”之说,并曰:“斯义也,闻之成都隐者。”足观宋史所载不虚。据《成都县志》所载:“二程过箍桶翁时地方,即是省城内之大慈寺。”
谯定传又载:“袁滋入洛,问易于颐,颐曰:‘易学在蜀耳,盍往求之?’滋入蜀访问,久之,无所遇,已而见卖酱薛翁于眉邛闾,与语大有所得。”我们细玩“易学在蜀”四字,大约二程在四川,遇着长于易的人很多,不止箍桶翁一人,所以才这样说。
段玉裁做富顺县知县,修薛翁祠,作碑记云:“……继读东莱吕氏撰常州志,有云。袁道洁闻蜀有隐君子名,物色之。莫能得,末至一郡,有卖香薛翁。旦荷芨之市,午辄扃门默坐,意象静深,道洁以弟子礼见,且陈所学,叟漠然久之,乃曰:‘经以载道,子何博而寡要也?’与语,未见复去。”宋史云“眉邛间”,吕氏云“至一郡”,皆不定为蜀之何郡县,最后读浚仪王氏《困学纪闻》云:“谯天授之易,得于蜀夷族曩氏,袁道洁之易,得于富顺监卖香薛翁,故曰:‘学无常师’。宋之富顺监,即今富顺县也,是其为富顺人无疑。”(见段玉裁《富顺县志》)究竟薛翁是四川何处人,我们无须深考,总之有这一回事,其人是一个平民罢了。(按宋史作卖酱,吕王作卖香,似应从吕王氏,因东莱距道洁不久,宋史则元人所修也。)
袁滋问易于伊川,无所得,与卖酱翁语,大有所得,这卖酱翁的学问,当然不小,《论语》上的隐者,如晨门、荷蒉、沮溺、丈人等,不过说了几句讽世话,真实学问如何,不得而知,箍桶翁和卖酱翁,确有真实学问表现,他二人易学的程度,至少也足与程氏弟兄相埒,卖酱翁仅知其姓薛,箍桶翁连姓亦不传,真是鸿飞冥冥的高人。
易学是二程的专长,二人语录中,谈及易的地方,不胜枚举。《宋史·张载传》称:“载尝坐虎皮,讲易水师,听者甚众,一夕,二程至,与论易,次日语人曰:‘比见二程,深明易理,吾所不如,汝可师之。’撤坐辍讲。”据此可见二程易学之深,然遇箍桶翁则敬谨领教,深为佩服,此翁之学问,可以想见。袁滋易学,伊川不与之讲授,命他入蜀访求,大约他在四川受的益很多,才自谦不如蜀人,于此可见四川易学之盛。
据《困学纪闻》所说,四川的夷族,也能传授高深的易学,可见那个时候,四川的文化是很普遍的,《易经》是儒门最重要之书,易学是二程根本之学,与四川发生这样的关系,这是很值得研究的。
(三)四川之道教
薛翁说袁道洁博而寡要,俨然道家口吻,他扃门默坐,意象静深,俨然道家举止,可见其时道家一派,蜀中也很盛。二程在蜀,当然有所濡染。
宋儒之学,据学者研究,是杂有方士派,而方士派,蜀中最盛,现在讲静功的人,奉《参同契》和《悟真篇》二书,为金科玉律,此二书均与四川有甚深之关系。
《悟真篇》是宋朝张伯端(字平叔号紫阳)所著。据他自序是熙宁己酉年,随龙国陵公到成都,遇异人传授。考熙宁己酉,即宋神宗二年,据伊川新作《先公太中传》称:“神宗即位年代,知汉州,熙宁中议行新法,州县嚣然,皆以为不可。公未尝深论也,及法出,为守令者奉行后,成都一道,抗议指其未便者,独公一人。”神宗颁行新法,在熙宁二年,即是张平叔遇异人传授之年,正是二程在四川的时候。平叔自序,有“既遇真筌,安敢隐默”等语。别人作的序有云:“平叔遇青城丈人于成都。”又云:“平叔传非其人,三受祸患。”汉州距成都只九十里,青城距成都,距汉州,俱只百余里,二程或者会与青城丈人或张平叔相遇,否则平叔既不甚秘惜其术,二程间接得闻也未可知。
现在流行的《参同契集注》,我们翻开一看,注者第一个是彭晓,第二个是朱子。彭晓字秀川,号真一子,仕孟昶为祠部员外郎,是蜀永康人。永康故治,在今崇庆县西北六十里。南宋以前,注《参同契》者十九家,而以彭晓为最先,通行者皆彭本,分九十一章,朱子乃就彭本,分上中下三卷,宁宗元年,蔡季通编置道州,在“寒泉精舍”与朱子相别,相与订正《参同契》,竟夕不寐,明年季通卒,越二年朱子亦卒,足见朱子晚年都还在研究《参同契》这种学说。
清朝毛西河和胡渭等证明:宋儒所讲,无极太极,河洛书是从华山道士陈抟传来。朱子解易,曾言“邵子得于希夷(即陈抟),希夷源流,出自《参同契》”。宋学既与《参同契》,发生这种关系,而注《参同契》之第一个人是彭晓,出在四川,他是孟昶之臣,孟昶降宋,距二程到川,不及百年,此种学说,流传民间,二程或许也研究过。
义和团之乱后,某学者著一书,说:“道教中各派,俱发源于四川,其原因就是由于汉朝张道陵,在四川鹤鸣山修道,其学流传民间,分为各派,历代相传不绝。”他这话不错,以著者所知,现在四川的学派很多,还有几种传出外省,许多名人俯首称弟子,这是历历可数的。逆推上去,北宋时候,这类教派当然很盛。二程在蜀当然有所濡染。
(四)四川之佛教
佛教派别很多,宋儒所谓佛学者,大概指禅宗而言,禅宗至六祖慧能而大盛,六祖言:“不思善,不思恶,正凭么时,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?”宋儒教人:“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。”宛然是六祖话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