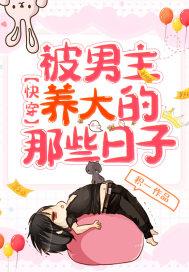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道职登峰,从王灵官开始 > 29淋尖踢斛小民难活(第1页)
29淋尖踢斛小民难活(第1页)
大夏王朝,幅员潦阔,南北气候和作物回然。
夏季收麦于北,秋季收稻于南,此为两税。
正税之外,又有草豆粟布等杂税,地方又有巧立名目,各色摊派
但对于农民而言最熟悉的,莫过于“淋尖踢斛”。
一石约百五十斤,合十斗,一斗合十升,这就是“升斗小民”。
交公粮的斛(hu)口小底大,装满后有四斗六十斤。但粮食是含水分的,晾干之后就会变轻,而且粮食运输也有风险,这就是“折耗”。
如果不超额征收,万一最后差一点完成不了任务,那就得差爷们自己掏腰包补上——但这是不可能的。
“淋尖踢斛”又名“脚踢淋尖”,就是在验收公粮时,斛顶必须堆出尖来。
堆尖之后用脚踢斛,斛顶上那部分粮食撒下来斛却不倒,流下来的粮食便美其名曰为“损耗”。
百姓再把斛中馀下的粮食拿去称重,无形中多交不少粮食,这种陋规已经是一笔半公开的灰色收入。
至于损耗多少才算够,只能说妙用存乎一心,全看差爷的心情。
当然,踢斛也是一项技术活。
踢这一脚斛不能倒,否则得耗时重装;
而如果踢得太多,难免民怨沸腾,群情激奋之下,说不定就要殴打税吏,这种事并不是没有发生过。
所以税收这种技术,就是拔最多的鹅毛,听最少的鹅叫。
而在王善看来,浑源县的这些税吏,毫无疑问是其中佼佼者。
王庄乡的村口,王勇哥的大儿子王方拿着籍册挨个点名,二儿子王刚则在一旁维持队伍的秩序。
衙门的税吏眼睛好象鹰隼一般,一边拿着毛笔在名单上勾画,一边盯着旁边官斛里的粮食。
一脚踹出去,农民们心惊肉跳,脸上是难以掩饰的肉痛。
而小吏也往往卡在这个微妙的节点——少了他没好处,多了眼前的几百个壮丁就要闹起来了。
“还好今年地里不缺水,粮食收成不错,不够的也都各家帮衬着借了粮。”
“王善,多亏了你啊。”
王勇哥拄着拐杖,坐在一旁的阴凉里。
他好歹是乡贤里老,不必事事亲力亲为。
这些小吏也怕老头儿万一中暑有个好歹,闹到衙门去,无意义的威风就没必要耍了。
“族长别这么说。就算没有我,以林知县的为人,也会约束这些酷吏。”
“新官上任三把火,我看这些人踹得没有往年用力,都存着几分小心。”
一旁的王善气息稍微急促,浑身热气腾腾。
他刚和村里青壮搬粮食过来,肩膀上垫着麻布,缝隙里还沾着几颗麦子。
目光扫过气势汹汹的小吏和面容苦涩的同乡,感同身受,又觉有几分庆幸。
若不是得到义夫牌匾免去一年税役,现在他也会在那长长的队伍里,焦急地张望,为税吏的鬼脚而胆战心惊,为可能发配的徭役坐立不安。
哪能象现在这样,和族长一边乘凉,一边感慨他人的悲欢?
王善没有忘记,这一切是短暂的。
等到正化七年一过,自己的门上虽然依旧挂着义夫牌匾,但却又要回到曾经为了温饱而挣命劳作的生活。
要改变这一切,必须进入县学,习武获得功名!
县学生员虽不免税,却能免家中两人徭役,这就有了最基础的保障。
等换上了一身襕衫,再来纳税的时候,你看这些吏员还敢不敢踹?
只怕是要陪着笑脸,叫一声“王老爷”
漫长的队伍缓缓挪动,太阳从东边走到了西边。
chapter_(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