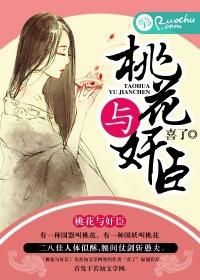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蜀山剑侠传(珍藏版) > 第二六一回 怨毒种灵禽 白骨穿心腾魁影 缠绵悲死劫 金莲度厄走仙童(第3页)
第二六一回 怨毒种灵禽 白骨穿心腾魁影 缠绵悲死劫 金莲度厄走仙童(第3页)
尤其听到阮征说是爱她,更是媚目流波,满脸欣慰之色。及至说到未几句上,想是会短离长,柔肠欲断,满腹悲苦,再也支持不住。始而翠黛含颦,隐蓄幽怨,渐渐语带哽咽。
到了未句“哥哥走吧”,竟然不胜凄楚,星眸乱转,泪随声下。人是那么美艳多情,声音那么凄婉,处境又如此壮烈悲苦,端的子夜鹃位,巫峡猿吟,无此凄凉哀艳。李洪九世修为的童贞有道之士,也被感动,心酸难过。
少女见阮征不肯收那二相环,不住以好言求告,满面愁苦,惶急万分,不禁破涕为笑道:“我为爱你大深,不借百计千方,屡以色身**。现虽蒙你见怜,允作名义夫妻,他年同修仙业,我也知你至诚君子,不会欺我,终觉为形势所迫,为解夙孽,不是真心相爱,想起前事,引为奇耻。今得见你至情流露,百死无恨。除不舍这长时之别外,只有更喜慰。料你二相环不肯收去,这件法宝,于你异日修为关系至大,我决不舍损伤我心爱丈夫防身之宝,但决阻我不住。为全此宝,说不得,只好拼受痛苦,以次而行了。”
“二嫂无须拙见!我来接应二哥,持有佛门至宝在此,你二人均不妨事。只请世嫂暂等三年,便与二哥同证仙业了。”话未说完,佛门至宝已先发出,化为一朵亩许大的千叶莲花宝座,飞向男女二人头上。李洪再掐灵诀一指,莲花上突涌起一圈佛光,照向少女身上。少女此时本是苦痛万分,眼看形神将化血云而散,忽见李洪现身,听出来的是丈夫好友。但知魔法厉害,万无解救,既不信一个幼童有此法力,又恐来人失陷,话未听完,便负痛急喊:“你那法宝无用!来人快走!”佛光已照向身上,立觉金芒掩耀,神铁无光,通体清凉,疼痛全止,魔法自解,全身金刀、金叉、金针之类纷纷坠地。事出意料,心中狂喜。同时瞥见前退侍女由魔宫左角蜂拥而来。为首一女,隔老远将手一扬,花林四外突然血焰飞扬,中夹千万金刀,潮水一般,向平台上涌到,大片园林立成刀山血海,李洪归路已断。少女见状,一声娇叱,将手一挥,四围血焰金刀便不再进。口中急喊:“哥哥还不快走,等待何时?”这原是转瞬间事:李洪早连宝座一齐飞向平台之上,不等少女说完,飞身上前,手拉阮征,另一只手一扬灵诀,莲座往下略沉,阮、李二人飞身其上。佛光随将二人罩住,宝座千层莲瓣齐放毫光,拥着二人,电也似疾,更不再由故道,冲破千层血浪金刀,往花林上空突围而出。耳闻身后风雷大作,宛如百万天鼓一齐怒鸣,声势惊人。回顾少女,手执一枚金环,由环中射出一道黄光,一晃分布开来,将血焰金刀阻住,似在断后神气。同时又闻远远传来一种钟磬之声,悠扬娱耳。
李洪料知尸毗老人已经警觉,血焰金刀已被少女阻住,正好逃走。刚飞出不远,忽想起小寒山二女尚在峰半崖洞之中潜伏。略一迟疑,猛听空中有一老人口音喝道:“孺子何来,竟敢犯我禁条么?”声才入耳,便见前面高空中悬下一条宽达十丈,长约百丈以上的黄光。当中站着一位老人,生得自发银髯,修眉秀目,狮鼻虎口,广额丰颐,面如朱砂,手白如玉。穿着一件火也似红的道袍,白袜红鞋。相貌奇古,身材高大,宛如画上神仙,手执一个白玉拂尘,挡住去路。相貌那样威严,面上却无怒色,手指二人道:
“你这娃儿虽然无知,这等胆大,倒也罕见。先不间你来历,我只问你:你救这人,欠我女儿三生孽债,尚未清偿,你们一走,就算完了么?”李洪法力甚高,年幼胆大,屡世修为,见多识广,人又灵慧机智,一见这等声势,知非易与。又因阮征乃屡世患难骨肉之交,知他成败安危,系此一举。本意委屈求全,但求免难,不肯操切从事。何况来时又经高人指教,竟把往日遇敌勇往直前之气去个干净,破例小心起来。当时躬身答道:
老人闻报大怒,喝道:“孺子大胆乃尔!我在此修炼千年,从无一人敢犯我一草一木。你来此救人,念在为友义气,本不想与你计较,略问数言,便即放走。你竟敢率人毁我灵景,伤我侍女。就此放你,情理难容。就算我女儿孽缘已解,也须将我灵景复原,还须问明情由,方可酌情释放。”话未说完,忽听谢琳在暗中插口笑道:“老人家在自修道千年,为何这么大火气?阮道友所欠乃是令爱孽缘,与你何干?逞能出头,已嫌多事。冤孽未解,也还可说,如今债主已自愿了结,反而怨你行事狠毒,你仍出头作梗,理更不通。如说毁你山中景物禁制,须要赔偿,那么阮道友与你并无冤仇,无故将他困禁两年,受尽金刀、魔火、风雷之厄,你将如何赔法?”老人已怒不可遏,厉声喝道:
“何方贼婢,敢在我面前饶舌强辩?”随将手中玉拂尘一挥,立有千百万朵血焰,灯花暴雨一般飞出,布满空中,将阮、李二人金莲宝座一齐围住。虽因佛光环绕,无法近身,但是上下四外已成一片血海。李洪心灵上立有警兆,知道老人魔法至高,自己法力新得,虽习禅功,功力尚差,一个冲不过去,全数被擒。所幸老人未自道名姓。心中愁急,方欲婉言分说,与之辩理,忽听谢琳传声语道:“洪弟,你不要慌,事情有我担待,只准备走好了。”阮征同也要挺身向前理论,闻言略一迟疑,二女七宝金幢已先发动。李深知谢琳近日性情法力,料将决裂,难于挽回,因受大方真人之惟恐做过了分,将来更难化解。一面传声密告二女,不可现身;而把灵峤三宝连同断玉钩同时施为。也不前攻,只将宝座四外护住,挡在金幢宝光之前,高声说道:“后辈不敢班门弄斧,只望老人家大度包容。三年之后,再与令婿同上仙山,负荆请罪。暂时我们告辞了。”
老人本极高明识货,明知金莲宝座乃西方至宝,李、阮二人根骨福慧平生仅见;阮征又孽冤已解,转祸为福;素性又最喜这等灵慧隽秀的幼童少年,本无伤害之意。此时追出拦阻,虽以千年威望所关,不愿来人随意出入禁地,事成之后从容而去,一半还是另有深心。不料小寒山二女久候李洪不至,谢琳首先不耐。又以阮征乃妙一真人九生高弟,昔年法力高强,并有两件至宝随身,稍差一点妖邪,闻名丧胆,望影而逃。此次为了犯过,逐出师门八十一年,在强敌林立,群邪环伺之下,竟以精诚毅力,历尽苦厄,排除万难。这最后一场冤孽更是厉害,有力难施,师长良友全都爱莫能助。终仗着至诚苦志,感化魔女,同保真元,化敌为友。人又生得那么英秀,前在峨眉仙府,曾听癞姑说起,此人在同辈仙侠中有第一美少年之称。不特一班异派妖邪**娃**欲得而甘心,便是海外女散仙,甘弃仙业欲谋永好的也大有人在。灵云姊妹未成道时,与之情分甚厚,历劫九生,终能守身如玉,以迄于今,又将这仙凡所不能解的夙世爱孽奇冤一朝化去。
事有凑巧,那丑女便是魔女恨其告发阮征,欲加毒打,后又逐出的侍女拉蛮。因为求荣反辱,怀恨在心。算计两年期满,阮征不从婚姻,魔女痴情,必将此人放走。为想讨好老人,近日常往伏伺。正与同党侍女阿鬕在一小峰之上密语窥探,却被二女隐形跑来听去。同时阮征和魔女正诉说前事,情致哀艳,令人心侧,二女大为感动。因听两侍女准备阮征一逃,立将埋伏全都发动,擒去惨杀,心已愤其残酷。跟着李洪发出金莲宝座,刚将分身解体魔法破去,两侍女也将埋伏引发。二女立时生气,顿忘杨瑾之诫,谢琳先将灭魔宝篆施展出来。谢缨又将碧蜈钩放出,化为两道翠虹飞将出去。因不肯轻用七宝金幢,魔宫禁制又极神妙,阿鬟本不至于受伤。偏生平台上魔女见阮、李二人还未起身,侍女已将禁制发动,惟恐情人受伤,又陷罗网,当时急怒交加,也未看清李洪有无同伴,猛以全力将所有禁制强行止住,双方恰是同时动手。拉蛮狡诈,一见主人身上刀叉飞针自行脱落,人也未伤,魔法全解,大出意外。小主人不死,不问阮征能逃与否,决不与己甘休,知事不妙,见势先逃。阿鬕骤不及防,竟为碧蜈钩斩断一臂,化道血光逃去。丑女拉蛮本往老人宫中告急,老人已经警觉追来。同时阮、李二人也飞身遁走,二女立即追去。这事本是一时疏忽,阴错阳差,老人又预有算计。假使无人告密,老人必定装作不知,双方问答几句,即可无事。无如丑女拉蛮本系老人记名弟子,因犯过恶,降为侍女,人极好狡,蓄有私心。自惭貌丑,老人又最恨**恶,自见阮征,便生忌妒。
谋害未成,反与魔女结怨,仇恨越深。巴不得有事,一见老人追出,随后赶来大声告发。
老人虽有通天彻地之能,只是嗔念未消,积习难忘,闻言自觉多年威望,情面难堪。
又听二女出语讥嘲,最奇是凭自己这么高法力,竟看不出对方形影,越发有气。刚刚出手将来人困住,本心迫令服输,稍加惩治,仍愿放走。哪知血焰刚涌上去,莲花宝座佛光骤盛,已出意外。紧跟着又涌现出一幢上具七宝的金霞,祥辉潋滟,瑞霭千重,将阮、李二人笼罩在内,血焰挨近,便即消散。认出此宝来历,只不知幢顶舍利己失。心方惊急,李洪又将灵峤三宝与断玉钩一齐发出,光芒万丈,奇辉电耀,挡在金幢之前。都是闻名多年的仙府奇珍,西方至宝,竟在此时突然出现。一任老人平昔自负,也由不得心生谨慎,急怒交加,嗔念与好胜之心也被激发。正待施展玄功变化,改变初衷,与敌一拼,忽听李洪以上说话,盛气渐平。又觉对方法宝如此厉害,纵然炼就不死之身,不致受什么伤害,但是此时尚可乘机下台,再若出手,一个制伏不住,盛名立堕,反而不美。
李洪先问:“老人家有何见教?”阮征接口说道:“岳父息怒。我与令爱虽无肌肤之亲,已有夫妇名分。蒙其深情厚爱,不特自解前孽,并允三年之后,与小婿同去海外合籍双修,同证仙业。今当孽消难满,蒙屡生良友解危脱困,冒犯威严,实非得已。所望岳父念在来人急于义侠,未知厉害,大度包容,使小婿重返师门,再事潜修,感恩不尽。”
老人把两道其白如霜的寿眉往上一扬,冷笑道:“此中因果,我原晓得。救人尚可酌情容恕,为何毁我灵景,伤我侍女?本来欲加惩处,现因我女在宫中苦苦哀求,拼舍一身为你们赎罪。如以为你们持有仙、佛两家至宝,便行自满,日后来人再犯我手,就难活命了。”
这时对面现出一圈银光,大约数亩,中现一座金碧辉煌、宛如神仙宫阙的魔宫洞府。
魔女跪在一个法坛之上,囚外尽是金刀魔火,围紧烧刺,正在哀声号位,哭求乃父宽纵来人,声音悲楚,惨不忍闻。阮征见状,慨然接口,厉声说道:“我不忍见此惨状。请速停止禁制,我束身待命,任凭宰割便了。”老人红脸上方转笑容,答道:“既允放你,决不食言。我女自作自受,以死相挟。此时虽然不免受伤,但亦无妨。你们去吧。”说到“去”字,把手一挥。先是光中刀火全清,只剩魔女娇声悲泣,委顿在地,柳悴花憔,奄然欲绝。同时四外血焰潜收,晴空万里,重返清明。老人也自隐去。只觉一股重如山海的绝大潜力由后涌来,推着宝座、金幢,比电还疾,往来路飞去,晃眼远出千里之外,方始停止。老人未句话的余音,犹复在耳。谢琳几次要想开口,均被李洪阻住,直到潜力收去。众人又飞行了一阵,算计途程已达二千里外,料知不会有事。刚把势子放缓,想要互叙别状以及各人经过,忽听破空之声,同时瞥见一道金光如长虹经天,横空飞来。
李洪与二女同声急呼:“大姊来了!”
来人已经飞近,光中现出一年约十八九岁的道装女子,正是峨眉四大女弟子中的齐灵云。见面把手一招,便往左近山头上飞去。众人料知有事,忙收遁光法宝,跟踪降落。
此符飞行千万里,顷刻即至,又当宇宙磁光最弱之时,当日便可到达。如过今天,磁光威力绝大,便有此符,也甚费事。并且你事完之后,日内还要重返中土,故非迅速不可。
此环尚有一枚在申屠师兄手中,他得了一丸西方神泥,与之融合,如能六环合用,威力更大。无如他日内也有急需,暂不能取。你我劫后重逢,尚有多少话说,请即起身,日后相见再作长谈吧。”阮征闻言大喜,随将法宝、灵符接过,一纵神光,往小南极飞去。
灵云又对谢、李三人说:“大咎山之行,由今天算起,应在第四天上。早去便生枝节,务要留意。洪弟虽然年幼,此行尚还无碍。倒是二妹眉宇间隐伏杀机。自来道长魔高,尤其二妹近习灭魔宝篆,法力虽然高强,也必从此多事。所望杀戒少开,遇事务从宽大,便可少却许多烦恼。属在知交,特为奉告,留意为幸。愚姊新近移居紫云宫,本意请去一游,无如远在东海,相隔数万里,往返费时,万一误事,反而不美。异日事完有暇,再奉邀一游吧。此三四日中,最好能寻一处知交姊妹,前往小聚,以待时至,往除毒手妖孽。以金幢威力,一日夜间即可将其消灭。如愿回转武夷等候更好。愚姊尚另有事,行再相见吧。”说完,作别自去。
谢琳笑道:“灵云姊姊人是极好,就嫌她稍为有点头巾气。洪弟是她前生爱弟,性情却不一样,这等淘气。”李洪未及答言,谢璎接口道:“琳妹此言不对。他虽宿根灵慧,今生毕竟年幼。可记得你我未到小寒山以前,不也是带着几分稚气么?”谢琳笑道:
“你还说他幼稚呢,平时那样好胜喜事,多大乱子,他都敢惹。可是适才对付老魔头,说那一套,何等文雅谦和,酸溜溜的。你我当初说得出来吗?可见他也是欺软怕硬,见景生情。不似寻常初生之犊,惯吃眼前亏呢。”李洪气道:“二姊专挖苦我,也不想想今天是甚情势?阮二哥和我多深交情,休说几句软话,为他脱难,再大委屈我也愿受。
如非有所顾忌,一任对方多凶,我要皱一皱眉头才怪。”谢琳把樱口一撇,笑道:“事后说狠话,谁相信你?像老魔头那高法力的人,方今能有几个?另换一人,自然你狠,何足为奇?”谢缨见李洪无话可答,赌气把小胖脸往侧一歪,假装看山,不再理睬。知道二人世交至好,无事常喜拌嘴。妹子心灵慧舌,妙语如珠,李洪稚气天真,一说不过,就生闷气,转眼就好,已成常事。便笑说道:“琳妹,话不是这样说。尸毗老人得道千年,法力兼有佛、道、正、邪诸家之长,实非小可。眼前各位长老尚且无人对他轻视,何况我们后生小辈?这次我们因候洪弟不至,前往窥探,本心不想为敌,不料无意中触动禁制,毁损好些灵景。他千年威望,不快自是人情,你不合出语讥嘲,越发激怒。当血焰猛压洪弟法宝,尚未施为之时,虽然西方至宝仍具极大威力,冲行其中,便不似毒手妖光云幕那么容易,我心灵上也有了警兆。幸我存有戒心,又知金幢舍利己失,未敢轻敌,无相神光不曾撤去,魔女恰在此时舍身求告,才得善罢。否则,以我今日观察,我三人结局,胜负正自难定呢。就以修道年龄而论,洪弟词意稍为卑下,也不为过。何况对方乃阮师兄的岳父,而洪弟所说不亢不卑,也甚得体呢。分明我姊妹不来,事更易了;这一来,反倒生出嫌怨。此时想起,真觉多此一行哩。”
“那么我们到哪里去呢?莫非在这荒山顶上露立四天么?”谢璎道:“如今各位姊妹道友,俱各奉命下山建立洞府,积修外功,都可以作主人。除幻波池,因听李伯父的口气,似乎不应再去外,余者哪里都可去,地方多着呢。”谢琳喜道:“我想起来了。前次峨眉开府,我姊妹几乎被于蜗的混元球装走,多亏半边大师赐我一根玄女针,才得转危为安,甚是感念。她门下武当七姊妹,又有五人与我们交好,分手时曾答应日后有便,往作良晤。山在鄂西,邻近四川,以我们飞行之速,往大咎山片刻可至,由彼动身,也颇方便。我意欲往作数日之聚,便践前约,不是好么?”谢缨拍手称妙。李洪却不愿意道:
“我不惯和女子同玩,武当门下尽是些女弟子,有甚意思?你们去,我不去。”谢琳笑道:“你敢不去,日后你再出花样淘气,我们再帮助你才怪。我姊妹不也是女的,你怎么也跟我们好呢?你刚到武夷拜师,因太幼小,好玩喜事,我们每去,你磨着出游,好姊姊喊个不住,哪一次不是我抱你同去?如今又不愿与女子同玩了,羞也不羞?你不知道石家姊姊她们人有多好,还不是和我们一样?”李洪也笑道:“莫非这也算是我的短处?引头带我出游,不也是你吗?第一次和妖人动手,还是你教的呢。去我便去,你要当着外人拿我取笑,我决不于,当时就走。心灯在我手上,误事你却莫怪。”谢嘤接口拦道:“你俩姊弟,每到一处就拌嘴。洪弟也是多余,我们比同胞骨肉还亲,当着外人只有夸你,怎会取笑?这里景物荒寒,久留无趣,我们走吧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