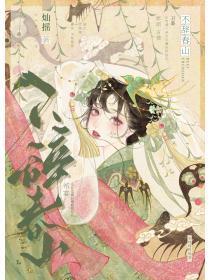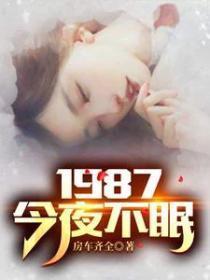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末世列车:百倍物资与多女主的传 > 第224章 流动的边界与没有终点的共生之路(第1页)
第224章 流动的边界与没有终点的共生之路(第1页)
作者“孤独的海星”推荐阅读《末世列车:百倍物资与多女主的传》使用“人人书库”APP,访问www。renrenshuku。com下载安装。跨族学院的边界线一首是孩子们争论的焦点。晶族孩子觉得应该用星尘晶画出闪烁的光带,石族孩子坚持要用大地石垒出坚固的石墙,争执了三个月,边界线反而成了片没人管的荒地,长满了野草。
“不如就留着吧。”阿禾在学院大会上提议,“让边界自己长出来。”
这个提议起初遭到反对——“没有边界会乱套!”“晶族的光会跑到石族的田!”但当孩子们发现,野草里长出了能同时吸收光与土能量的“共生草”,当晶族的能量灯不小心飘到石族的工具房,反而让生锈的工具重新发亮,当石族的泥土被雨水冲到晶族的花园,让星尘花长得更茂盛时,反对声渐渐消失了。
边界成了最热闹的地方。晶族在这里搭了“光桥”,石族在旁边挖了“土洞”,光桥的影子落在土洞里,会开出会发光的蘑菇;土洞的潮气漫到光桥上,会结出能发光的露珠。孩子们在光桥和土洞间钻来钻去,晶族孩子教石族孩子用能量编织光网,石族孩子教晶族孩子用泥土捏能量罐,没人再在乎“这是晶族的地”还是“那是石族的界”。
莉诺的实验室就建在边界旁。她最近在研究“能量转化器”——能把晶族的光能转成石族需要的土能,也能把土能转成光能。“以前觉得能量只能单向流动,”她调试着仪器,“现在才发现,它们像水一样,能互相绕着走。”
岩松在旁边的田里种了“双能稻”,稻穗一半是银色的,结星尘米;一半是褐色的,结大地米。“你看这稻根,”他拔起一株,根系上缠着银色和褐色的须,“它们自己会找平衡,不用我们瞎操心。”
这天,星盟派来视察的长老团到了。为首的长老看着没有边界线的学院,眉头紧锁:“连边界都没有,怎么保证两族的特色?再这样下去,晶族会忘了怎么凝聚强光,石族会丢了大地的沉稳!”
话音刚落,远处突然传来孩子们的惊呼。只见边界处的共生草突然疯长,藤蔓缠成了道拱门,拱门上的花同时亮起银褐两色光,把长老团的身影笼罩其中。光影里,出现了叶舟和石青芜的虚影——那是大地藤记录的能量影像。
“特色不是靠边界框出来的。”叶舟的虚影举着光剑,剑光照亮了石青芜的盾,“我的剑再利,没她的盾托着,早断了。”
石青芜的虚影敲了敲盾:“我的盾再稳,没他的光照着,早被暗物质蚀穿了。”
虚影渐渐淡去,共生草的拱门却更亮了。长老团里有人认出,那光剑的纹路和石青芜盾上的花纹,合在一起正是星盟最初的徽章图案。
“当年建立星盟,”阿禾走上前,指着拱门下玩耍的孩子们——晶族孩子帮石族孩子修理光桥,石族孩子给晶族孩子递大地米做的点心,“就是为了让光和土能一起发光,而不是各自在角落里黯淡。”
长老们沉默了。他们看着那些在“无边界”里自由穿梭的孩子,看着既能发强光又能抗冲击的双能稻,看着光桥与土洞之间自然形成的能量循环,突然明白:所谓“特色”,从不是孤立的标签,而是在共生中更清晰的自我。
视察结束时,为首的长老在留言簿上写下:“边界是用来连接的,不是用来隔开的。”他把随身的星盟徽章摘下来,嵌在共生草的拱门上,徽章的光与花草的光融在一起,再也分不出彼此。
那天晚上,跨族学院的孩子们举办了场“无边界派对”。他们把晶族的光琴和石族的土鼓凑在一起演奏,发现光琴的旋律能让土鼓的声音更浑厚,土鼓的节奏能让光琴的调子更悠长;他们用星尘粉和大地泥混合,捏出了会发光的泥人,泥人身上的纹路,一半像光剑,一半像盾牌。
阿禾站在拱门下,看着烈风举着相机拍照,镜头里,莉诺和岩松正在给双能稻浇水,两人的影子在地上交叠成一个完整的圆。她想起时光信箱里最新的一封信,是个晶族小女孩写的:“十年后,希望边界上的草能长到天上去,这样我们就能踩着草,到星星上找叶舟爷爷和石青芜奶奶,告诉他们,我们把学院建得比图纸上还好。”
夜空的星星很亮,像无数双含笑的眼睛。阿禾知道,这条共生之路没有终点,就像光与土永远在流动,就像孩子们的笑声永远在生长,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温柔,总会被时光酿成更甜的酒。
而最好的边界,从来不是画出来的线,是心与心之间,那道愿意为彼此敞开的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