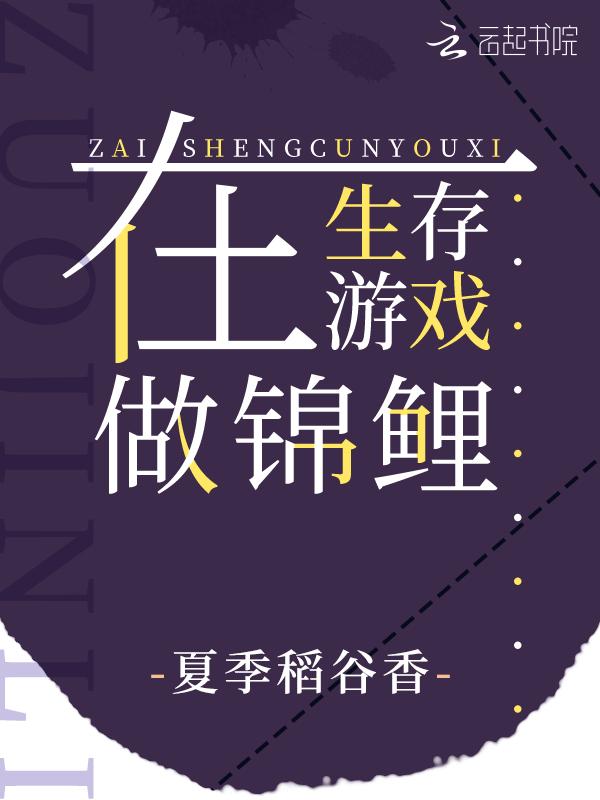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帝妻[重生] > 230240(第18页)
230240(第18页)
“若不是勤政殿,就该出宫了。”燕姒眼神尤其无辜,“只有勤政殿,才能脱离是非,再或陛下像方才臣女所说的那般,放臣女出宫回家。”
“放出宫不行。”唐峻脸色肃然道。
燕姒说:“陛下从未想过要对殿下赶尽杀绝,可高壁镇声势浩大地一局棋,为的便是做给天下人看,您初登皇位,镇得住精兵强将,谋略不逊任何人,只要臣女一日还在宫中,陛下固权才能见到成效,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,臣女明白的,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[1],您此时觉着楚家闹腾是小事,殊不知楚家由先帝一力扶起,实力并不容小觑,眼下边南军械补给,您且看着,并不会那般顺利。”
“他楚家还能翻了天不成?掌户部的权把持银库不假,但他的权是谁给他的?是皇室!”唐峻怒道。
燕姒立即起身跪拜平息唐峻怒火,只言片语,全踩在刀尖上。
“新臣少,楚家使绊子坏陛下的事,您目前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,户部尚书一职干系重大,您没有合适的人来替。”
“朕需要时日。”唐峻咬牙切齿:“军械补给不容半点差池,谁要影响战事,朕绝不姑息!有朕在前边撑着,你放心,坤宁宫至今日后,再不会有什么让你不顺心让于家不舒坦的事发生,先起……”
“陛下。”燕姒不想他话锋转得如此快,只好打断道:“柳阁老病逝前,您去过柳宅。”
这不是燕姒发出的疑问,而是肯定,唐峻瞳孔顿缩,要去扶人的手僵在了半空中。
燕姒又道:“臣女知道此事,陛下不该惊讶。”
唐峻垂首盯着燕姒头顶,未几才找回自己的声音。
“说下去——”
燕姒宠辱不惊道:“臣女出宫那日,也曾去过。”
唐峻低声道:“朕不是让……”
“让金羽卫暗中包围了整个柳宅。”燕姒接过他的话,道:“阁老一生清廉公正,若真要说有何偏私,她临终前,却选择了陛下,她坚持她是寿终正寝,可陛下心知肚明。”
唐峻倒抽一口冷气,忽觉头痛欲裂起来,他现在终于明白长公主府传信的目的了,他不得不再次对眼前人正眼相待,他想他也终于明白,为什么唐绮私自返都,只遵照柳老去前的遗言办过了丧事,再没滞留都中。
而他有一处却不明白。
他心里有愧,声音都失了底气,哑声道:“你如何知晓朕去过柳宅的?朕去柳宅时,你该还在坤宁宫里!”
燕姒闭眼不答,叹息声缥缈难捉。
“陛下没有绝对信得过的人。”燕姒直白道:“您无亲长依托,全靠血脉正统,先帝遗命,才继承了大统,所以您忍气吞声包容远北,亲自甄选各地征银节度使,布局高壁,不惜手足之情破碎,也要压住朝中异声。您勤于政务,连年节里都不得闲,是因您怕。您怕托不起这唐国江山。”
唐峻心口犹如针扎,把住椅扶手的手攥得青筋暴起。
燕姒忽然说:“您可以信我一次,我进勤政殿,绝无异心,只为成全先辈,若您还不信,我可以同您说一个迄今鲜为人知的秘密……”
唐峻不自主地被她牵着走,好奇道:“什么鲜为人知的秘密?”
燕姒微微抬起头:“当初于家让我认祖归宗,姜家大闹了一场,而我生母至今未曾露过面,是有原因的。”
唐峻好奇心更甚了,“原因?”
燕姒道:“我生母其人,乃是前朝鸿儒荀万森荀大家的孙女。”
唐峻惊站起身:“你说你生母是谁?!”
燕姒微微扬起下巴:“荀万森的孙女。”
唐峻出生的时候,成兴帝已登基称帝两年余,因是长子的缘故,他幼年颇得喜爱,曾在唐兴口中听过不少关于荀万森的事。
其中唐峻最爱听的一段,便是那位鸿儒大家晚年的穷途末路。
传说里。
那位老者,携东宫派系群臣跪于端门,只为求最后一个面圣之机。
他挺着宁折不弯的脊梁,隔一条千步道,面向三千玉阶上疑似摇摇欲坠的明和殿,忍不住老泪纵横。
他哭的是,纵使满腹经纶,也会沦到束手无策。
转瞬,时代已逝。
唐峻跌坐回椅子上,稍一联想前因后果,而后乏力地笑了。
“难怪你生母从不出现,难怪周冲之子冒犯你的案子来得突然又诡异,难怪那时候阿绮要跟我联手为前太子翻案,搞垮国舅爷周冲。都是报应,周家应得的报应。”
“外戚是祸患,阁老辞世也很突然,楚家现在无非同陛下堵着气,仗势胡作非为。”燕姒跪直道:“您可以信我的,我以先辈之名在此起誓,一切以唐国大局为重,替陛下分忧解难绝无二话。”
唐峻看不明白这个于家荀家的后辈,不知她何来如此自信,敢句句见血,说到点子上,又豁得出去。
他茫然道:“你就没有自己的所图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