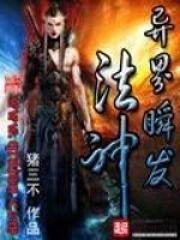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让你做短视频,你科普黑暗森林 > 第174章 人类登月一(第1页)
第174章 人类登月一(第1页)
做完《生態建筑》,李水旺开始做新一期视频——《人类登月》:
55年前,尼尔?阿姆斯特朗和巴兹?奥尔德林成为首批踏上月球的人类。他们与麦可?柯林斯一同乘坐阿波罗11號返回地球,在亲眼见证此次登月的6。5亿人心中,以及我们这些后来出生的人心中,开启了从地球通往星辰的道路。如今,尼尔?阿姆斯特朗和麦可?柯林斯已离世,而95岁高龄的奥尔德林將军仍是在世的传奇人物。阿波罗11號三位太空人的功绩將被世人永远铭记,但奥尔德林在太空领域的贡献,绝非始於也绝非止於那次登月任务。他是美国国家航天协会的理事,对协会许多长期会员而言,他就像家人一样——既是志同道合的倡导者,也是致力於铺平通往太空之路的科学家。为实现这一目標,他研发了眾多项目,並牵头开展了多项努力。今天,我们將聚焦其中一个项目——火星循环飞行器,如今它更常被称为“奥尔德林循环飞行器”。这是一种能够低成本、安全地往返地球与火星,运送大量货物的太空飞行器。
我认为,巴兹作为科学家和工程师所付出的努力,很容易被那次具有歷史意义的登月任务所掩盖。1951年,他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,获得机械工程学位;之后在韩战期间执行了66次战斗任务;1963年,他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,其博士论文题目为《载人太空飞行器交会的空间视线制导技术》。隨后,美国空军將他指派到“双子座计划”。1966年,他与吉姆?洛弗尔一同执行了双子座12號任务,后来两人均参与了阿波罗计划,其中洛弗尔担任了“命运多舛”的阿波罗13號任务的指令长。值得一提的是,在双子座计划的最后一次任务中,当飞船的计算机出现故障时,正是奥尔德林用六分仪和铅笔导航,成功与“阿金纳”目標飞行器实现交会;同时,他还完成了人类首次完全成功的太空行走,顺利完成了一系列被认为对阿波罗计划推进至关重要的任务。即便他此后未在太空探索与发展领域再有任何贡献,他在太空史上的地位也已稳固不朽。但正如前文所述,在那之后,他依然活跃在航天领域,包括长期担任美国国家航天协会理事——而我有幸担任该协会的会长——同时他还参与了火星协会指导委员会的工作。
说到火星,1985年,奥尔德林提出了一种太空飞行器轨道概念,即“奥尔德林循环飞行器”。他与他人合作完善这一概念,发表了相关论文,並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替代方案。但究竟什么是循环飞行器呢?简单来说,循环飞行器有时也被称为“循环城堡”,这一名称源於其隱含的角色与用途——它本质上就是在地球周边太空与火星轨道之间往返运送物资的“摆渡船”。一旦建造出一艘或一对循环飞行器,並將它们送入特定的轨道模式,它们就能反覆绕经地球和火星,自身无需再消耗更多燃料,最多只需少量燃料进行微小的轨道修正(不过,我们今天也会探討有动力驱动的循环飞行器版本)。这意味著,循环飞行器可以携带大量的防护层,以及船员在行星间航行所需的各类设备——但这些设备无需被运送到行星表面。如此一来,我们只需发射一艘轻型穿梭机,搭载执行任务的船员即可,无需携带笨重的辐射防护层,也无需携带大量水、空气,或是用於循环利用、净化这些资源的设备。
“循环城堡”配备了充足的物资,能够应对太空辐射、微陨石撞击以及太空真空环境的长期“考验”。我们预计,早期的循环飞行器可能功能相对简陋,但后期的循环飞行器或许会配备可旋转的舱段,以通过自旋產生人工重力;还可能利用水资源养殖鱼类和藻类作为食物来源,甚至建造游泳池,並持续种植新鲜的农作物——这不仅有助於循环利用二氧化碳,还能为船员提供一片充满生机的绿色空间。当抵达火星时,搭载船员的小型穿梭机会脱离循环飞行器,飞往火星表面或火星轨道上的空间站,隨后开展既定任务。理想情况下,在执行一两次任务后,火星表面將建成核反应堆,具备空气、水和燃料的生產能力,以便在数月后为返回轨道的穿梭机补充燃料。当然,如果只使用一艘循环飞行器,那么两次任务之间可能需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(数月之久)。
此外,循环飞行器本身也完全可以配备核反应堆作为动力源,这样的飞行器能够搭载100多人的船员团队,甚至可能搭载更多人——具体载客量取决於飞行器的规模。它们也可能高度自动化,在首次测试飞行时便可携带货物进行投放。循环飞行器依靠的是最小能量转移轨道,本质上是围绕太阳形成一个狭长的偏心轨道,在两个天体(此处指地球和火星)之间运行。以火星循环飞行器为例,它从地球飞往火星需要5个月,从火星继续向外飞行、越过火星轨道需要16个月,再从火星轨道返回地球轨道又需要5个月,之后每26个月重复一次这一周期。
我可以用一个类比来解释:这就像一列不停车的大型空火车,行驶在一条固定的风景线路上。要將人员、设备和物资运送到循环飞行器上,或是从循环飞行器上运下来,仍需像往常一样消耗燃料,但一旦登上循环飞行器,这段旅程就有了宽敞舒適的生活空间。而且,那些用於5个月航行的重型设备和可循环利用物资,只需运送一次即可。人们通常建议使用两艘运行在不同周期的奥尔德林循环飞行器,以缩短往返行程的时间——一艘用於前往火星,另一艘用於返回地球。即便在遥远的未来,我们拥有了速度更快的太空飞行器推进系统,能够以巨大的能量消耗实现一周內往返火星(这对旅客来说无疑是绝佳选择),通过循环飞行器运送货物或不急於赶路的旅客,依然能带来巨大的便利。
与太空发射窗口的常规情况一样,时间安排仍是一个难题,但通过提前发射进入太空,我们可以避开天气问题的影响。当然,若错过了与循环飞行器的交会窗口,问题就会出现——之后或许需要消耗更多燃料才能追赶上去。不过,交会窗口的时间跨度並不算特別紧凑;但如果火星轨道上没有可供返回的空间站,那么就只能再次降落在这颗红色星球上。这也是我倾向於支持採用循环飞行器开展稳健任务的原因之一:同时配备火星轨道空间站和火星表面永久基地,只需定期更换船员即可。这种配置意味著我们拥有更多的冗余方案和备用计划,而在规划长达数亿英里、持续数百天的太空旅行时,冗余方案再多也不为过。
这种(循环飞行器)方案並不仅限於地球与火星之间的航行,它適用於任意两颗行星之间。我们之前提到“地球周边太空”而非“地球”,是因为循环飞行器可能运送的是来自月球或各类太空基地的物资,而非直接来自地球。因此,我们完全可以建造地球-金星循环飞行器、地球-土星循环飞行器,甚至火星-木星循环飞行器——后者或许能將木星冰卫星上的挥发性物质运回火星,用於火星的地球化改造或类地球化改造作业。
循环飞行器也非常適用於往返木星的卫星——木星周边的辐射极强,因此,乘坐防护层较薄、燃料消耗较少的穿梭机进行短途飞行,抵达配备更厚重防护层的循环飞行器,再进行长途航行,无疑是理想选择。它们也是核推进技术的理想应用对象,因为循环飞行器无需非常靠近行星,可以使用离子推进器或其他低推力、高效率的发动机。实际上,循环飞行器还可以设计成能为离开它的穿梭机提供少量助推,以帮助其节省燃料,之后再通过某种方式恢復之前“借出”的动量。
除了从行星获取燃料,我们还可以在卫星上生產燃料,然后將燃料运送到轨道燃料库或循环飞行器上,为穿梭机补充燃料。说到卫星,循环飞行器的运行模式不仅適用於围绕恆星运行的两颗行星,也適用於围绕同一颗行星运行的两颗卫星,甚至適用於小行星之间。
这种“循环城堡”能极大地提升木星卫星之间贸易的可行性:卫星之间的循环周期更短,而额外的防护层在这种环境下堪称“救命符”。它们还可以储存冰物质,转交给往返於木星-火星、木星-地球的循环飞行器,甚至是往返於木星-小行星带的循环飞行器。核动力驱动的循环飞行器可以在漫长的航行过程中,利用多余的能量將这些冰物质转化为火箭燃料,同时补充自身的推进剂。实际上,这些冰物质可以通过无人驾驶的舱体、火箭运输,或是从木卫三或木卫二通过质量投射器发射出去,隨后被卸载到燃料库中,供穿梭机获取水、燃料、空气或其他所需物资——这其中甚至可能包括循环飞行器上种植的多余食物。
在椭圆轨道上运行时,飞行器在返程段本质上是“坠落”向目標天体,飞行速度会逐渐加快;而当它绕过主天体並再次向外飞行时,速度又会减慢,因为重力会试图將其拉回。这意味著,在飞行器运行到两颗目標天体中较远的那颗外侧、相对枯燥的航行阶段,其速度会较低。因此,除了负责维护的船员外,我们不会让其他人在这段时间待在飞行器上。接下来,我们將很快探討前往其他行星的长途航行会面临哪些情况,以及前往月球的更短途航行方案。
循环飞行器的大部分航行时间都处於“死寂”的太空中。这类飞行器可能高度自动化,设计初衷就是仅在往返两颗天体的航行阶段搭载人员,其余时间则处於空载状態。循环飞行器的轨道周期是两颗天体会合周期(synodicperiod)的整数倍,或者说,当两颗天体再次达到会合位置时,循环飞行器也会回到相应轨道位置。会合周期指的是两颗天体再次回到相对彼此相同位置所需的时间。
地球绕太阳公转的速度远快於火星:地球公转一周需要365天,而火星需要587天。但地球需要多绕几周才能追上一直在移动的火星,因此,地球和火星都需要转过远超360°的角度,才能完成一次完整的会合周期——这一周期为780天,即2。135年、25。6个月或111周。颇具讽刺意味的是,在所有行星中,火星的会合周期是最不利於安排发射窗口的之一,仅次於金星(金星的会合周期为584天,即1。6年)。小行星带內目標天体的会合周期通常约为一年半,而地球与其他天体之间的循环飞行器轨道周期则略多於一年——因为这些天体绕太阳公转的速度非常慢,地球只需多绕一周多一点就能追上它们,而此时这些天体甚至还未完成一周公转。
离太阳最近、公转速度最快的行星——水星是个例外,其会合周期仅为116天;我们的月球会合周期则为29。5天(这一点很实用,因为两次满月之间的间隔就是这么久)。不过,月球绕地球公转360°实际上只需27。3天,而在这段时间里,地球会继续绕太阳公转一段距离,因此,月球需要额外53小时才能回到与太阳、地球呈一条直线(月球位於地球背向太阳一侧)的满月位置。
地球的公转周期为365天,因此地球与外行星的会合周期分別为:与木星399天、与土星378天、与天王星370天、与海王星368天、与冥王星367天。但这並不意味著往返这些行星的航行能有这么快——飞行器的公转轨道半径必须大於目標行星的轨道半径,因此,整个循环周期必然会比外行星自身的公转周期更长(木星的公转周期约为12年,冥王星则长达数百年)。此外,循环飞行器每次经过行星时,也不一定会非常靠近行星。
做完《生態建筑》,李水旺开始做新一期视频——《人类登月》:
55年前,尼尔?阿姆斯特朗和巴兹?奥尔德林成为首批踏上月球的人类。他们与麦可?柯林斯一同乘坐阿波罗11號返回地球,在亲眼见证此次登月的6。5亿人心中,以及我们这些后来出生的人心中,开启了从地球通往星辰的道路。如今,尼尔?阿姆斯特朗和麦可?柯林斯已离世,而95岁高龄的奥尔德林將军仍是在世的传奇人物。阿波罗11號三位太空人的功绩將被世人永远铭记,但奥尔德林在太空领域的贡献,绝非始於也绝非止於那次登月任务。他是美国国家航天协会的理事,对协会许多长期会员而言,他就像家人一样——既是志同道合的倡导者,也是致力於铺平通往太空之路的科学家。为实现这一目標,他研发了眾多项目,並牵头开展了多项努力。今天,我们將聚焦其中一个项目——火星循环飞行器,如今它更常被称为“奥尔德林循环飞行器”。这是一种能够低成本、安全地往返地球与火星,运送大量货物的太空飞行器。
我认为,巴兹作为科学家和工程师所付出的努力,很容易被那次具有歷史意义的登月任务所掩盖。1951年,他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,获得机械工程学位;之后在韩战期间执行了66次战斗任务;1963年,他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,其博士论文题目为《载人太空飞行器交会的空间视线制导技术》。隨后,美国空军將他指派到“双子座计划”。1966年,他与吉姆?洛弗尔一同执行了双子座12號任务,后来两人均参与了阿波罗计划,其中洛弗尔担任了“命运多舛”的阿波罗13號任务的指令长。值得一提的是,在双子座计划的最后一次任务中,当飞船的计算机出现故障时,正是奥尔德林用六分仪和铅笔导航,成功与“阿金纳”目標飞行器实现交会;同时,他还完成了人类首次完全成功的太空行走,顺利完成了一系列被认为对阿波罗计划推进至关重要的任务。即便他此后未在太空探索与发展领域再有任何贡献,他在太空史上的地位也已稳固不朽。但正如前文所述,在那之后,他依然活跃在航天领域,包括长期担任美国国家航天协会理事——而我有幸担任该协会的会长——同时他还参与了火星协会指导委员会的工作。
说到火星,1985年,奥尔德林提出了一种太空飞行器轨道概念,即“奥尔德林循环飞行器”。他与他人合作完善这一概念,发表了相关论文,並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替代方案。但究竟什么是循环飞行器呢?简单来说,循环飞行器有时也被称为“循环城堡”,这一名称源於其隱含的角色与用途——它本质上就是在地球周边太空与火星轨道之间往返运送物资的“摆渡船”。一旦建造出一艘或一对循环飞行器,並將它们送入特定的轨道模式,它们就能反覆绕经地球和火星,自身无需再消耗更多燃料,最多只需少量燃料进行微小的轨道修正(不过,我们今天也会探討有动力驱动的循环飞行器版本)。这意味著,循环飞行器可以携带大量的防护层,以及船员在行星间航行所需的各类设备——但这些设备无需被运送到行星表面。如此一来,我们只需发射一艘轻型穿梭机,搭载执行任务的船员即可,无需携带笨重的辐射防护层,也无需携带大量水、空气,或是用於循环利用、净化这些资源的设备。
“循环城堡”配备了充足的物资,能够应对太空辐射、微陨石撞击以及太空真空环境的长期“考验”。我们预计,早期的循环飞行器可能功能相对简陋,但后期的循环飞行器或许会配备可旋转的舱段,以通过自旋產生人工重力;还可能利用水资源养殖鱼类和藻类作为食物来源,甚至建造游泳池,並持续种植新鲜的农作物——这不仅有助於循环利用二氧化碳,还能为船员提供一片充满生机的绿色空间。当抵达火星时,搭载船员的小型穿梭机会脱离循环飞行器,飞往火星表面或火星轨道上的空间站,隨后开展既定任务。理想情况下,在执行一两次任务后,火星表面將建成核反应堆,具备空气、水和燃料的生產能力,以便在数月后为返回轨道的穿梭机补充燃料。当然,如果只使用一艘循环飞行器,那么两次任务之间可能需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(数月之久)。
此外,循环飞行器本身也完全可以配备核反应堆作为动力源,这样的飞行器能够搭载100多人的船员团队,甚至可能搭载更多人——具体载客量取决於飞行器的规模。它们也可能高度自动化,在首次测试飞行时便可携带货物进行投放。循环飞行器依靠的是最小能量转移轨道,本质上是围绕太阳形成一个狭长的偏心轨道,在两个天体(此处指地球和火星)之间运行。以火星循环飞行器为例,它从地球飞往火星需要5个月,从火星继续向外飞行、越过火星轨道需要16个月,再从火星轨道返回地球轨道又需要5个月,之后每26个月重复一次这一周期。
我可以用一个类比来解释:这就像一列不停车的大型空火车,行驶在一条固定的风景线路上。要將人员、设备和物资运送到循环飞行器上,或是从循环飞行器上运下来,仍需像往常一样消耗燃料,但一旦登上循环飞行器,这段旅程就有了宽敞舒適的生活空间。而且,那些用於5个月航行的重型设备和可循环利用物资,只需运送一次即可。人们通常建议使用两艘运行在不同周期的奥尔德林循环飞行器,以缩短往返行程的时间——一艘用於前往火星,另一艘用於返回地球。即便在遥远的未来,我们拥有了速度更快的太空飞行器推进系统,能够以巨大的能量消耗实现一周內往返火星(这对旅客来说无疑是绝佳选择),通过循环飞行器运送货物或不急於赶路的旅客,依然能带来巨大的便利。
与太空发射窗口的常规情况一样,时间安排仍是一个难题,但通过提前发射进入太空,我们可以避开天气问题的影响。当然,若错过了与循环飞行器的交会窗口,问题就会出现——之后或许需要消耗更多燃料才能追赶上去。不过,交会窗口的时间跨度並不算特別紧凑;但如果火星轨道上没有可供返回的空间站,那么就只能再次降落在这颗红色星球上。这也是我倾向於支持採用循环飞行器开展稳健任务的原因之一:同时配备火星轨道空间站和火星表面永久基地,只需定期更换船员即可。这种配置意味著我们拥有更多的冗余方案和备用计划,而在规划长达数亿英里、持续数百天的太空旅行时,冗余方案再多也不为过。
这种(循环飞行器)方案並不仅限於地球与火星之间的航行,它適用於任意两颗行星之间。我们之前提到“地球周边太空”而非“地球”,是因为循环飞行器可能运送的是来自月球或各类太空基地的物资,而非直接来自地球。因此,我们完全可以建造地球-金星循环飞行器、地球-土星循环飞行器,甚至火星-木星循环飞行器——后者或许能將木星冰卫星上的挥发性物质运回火星,用於火星的地球化改造或类地球化改造作业。
循环飞行器也非常適用於往返木星的卫星——木星周边的辐射极强,因此,乘坐防护层较薄、燃料消耗较少的穿梭机进行短途飞行,抵达配备更厚重防护层的循环飞行器,再进行长途航行,无疑是理想选择。它们也是核推进技术的理想应用对象,因为循环飞行器无需非常靠近行星,可以使用离子推进器或其他低推力、高效率的发动机。实际上,循环飞行器还可以设计成能为离开它的穿梭机提供少量助推,以帮助其节省燃料,之后再通过某种方式恢復之前“借出”的动量。
除了从行星获取燃料,我们还可以在卫星上生產燃料,然后將燃料运送到轨道燃料库或循环飞行器上,为穿梭机补充燃料。说到卫星,循环飞行器的运行模式不仅適用於围绕恆星运行的两颗行星,也適用於围绕同一颗行星运行的两颗卫星,甚至適用於小行星之间。
这种“循环城堡”能极大地提升木星卫星之间贸易的可行性:卫星之间的循环周期更短,而额外的防护层在这种环境下堪称“救命符”。它们还可以储存冰物质,转交给往返於木星-火星、木星-地球的循环飞行器,甚至是往返於木星-小行星带的循环飞行器。核动力驱动的循环飞行器可以在漫长的航行过程中,利用多余的能量將这些冰物质转化为火箭燃料,同时补充自身的推进剂。实际上,这些冰物质可以通过无人驾驶的舱体、火箭运输,或是从木卫三或木卫二通过质量投射器发射出去,隨后被卸载到燃料库中,供穿梭机获取水、燃料、空气或其他所需物资——这其中甚至可能包括循环飞行器上种植的多余食物。
在椭圆轨道上运行时,飞行器在返程段本质上是“坠落”向目標天体,飞行速度会逐渐加快;而当它绕过主天体並再次向外飞行时,速度又会减慢,因为重力会试图將其拉回。这意味著,在飞行器运行到两颗目標天体中较远的那颗外侧、相对枯燥的航行阶段,其速度会较低。因此,除了负责维护的船员外,我们不会让其他人在这段时间待在飞行器上。接下来,我们將很快探討前往其他行星的长途航行会面临哪些情况,以及前往月球的更短途航行方案。
循环飞行器的大部分航行时间都处於“死寂”的太空中。这类飞行器可能高度自动化,设计初衷就是仅在往返两颗天体的航行阶段搭载人员,其余时间则处於空载状態。循环飞行器的轨道周期是两颗天体会合周期(synodicperiod)的整数倍,或者说,当两颗天体再次达到会合位置时,循环飞行器也会回到相应轨道位置。会合周期指的是两颗天体再次回到相对彼此相同位置所需的时间。
地球绕太阳公转的速度远快於火星:地球公转一周需要365天,而火星需要587天。但地球需要多绕几周才能追上一直在移动的火星,因此,地球和火星都需要转过远超360°的角度,才能完成一次完整的会合周期——这一周期为780天,即2。135年、25。6个月或111周。颇具讽刺意味的是,在所有行星中,火星的会合周期是最不利於安排发射窗口的之一,仅次於金星(金星的会合周期为584天,即1。6年)。小行星带內目標天体的会合周期通常约为一年半,而地球与其他天体之间的循环飞行器轨道周期则略多於一年——因为这些天体绕太阳公转的速度非常慢,地球只需多绕一周多一点就能追上它们,而此时这些天体甚至还未完成一周公转。
离太阳最近、公转速度最快的行星——水星是个例外,其会合周期仅为116天;我们的月球会合周期则为29。5天(这一点很实用,因为两次满月之间的间隔就是这么久)。不过,月球绕地球公转360°实际上只需27。3天,而在这段时间里,地球会继续绕太阳公转一段距离,因此,月球需要额外53小时才能回到与太阳、地球呈一条直线(月球位於地球背向太阳一侧)的满月位置。
地球的公转周期为365天,因此地球与外行星的会合周期分別为:与木星399天、与土星378天、与天王星370天、与海王星368天、与冥王星367天。但这並不意味著往返这些行星的航行能有这么快——飞行器的公转轨道半径必须大於目標行星的轨道半径,因此,整个循环周期必然会比外行星自身的公转周期更长(木星的公转周期约为12年,冥王星则长达数百年)。此外,循环飞行器每次经过行星时,也不一定会非常靠近行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