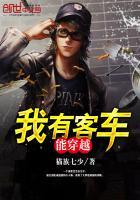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我要当大官 > 第二百三十一章 朕还能走到对岸吗(第3页)
第二百三十一章 朕还能走到对岸吗(第3页)
她终于明白,邓伦为何选择消失。因为他知道,唯有成为传说,才能让信念超越个体生死。他的声音不再属于自己,而是化作了风、雨、童谣、炊烟,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每一寸肌理。
第二天,她召集了北京地区的所有“静默信使”成员,在地下防空洞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。灯光昏黄,墙壁潮湿,三十多人围坐一圈,大多是教师、图书管理员、退休编辑、民间艺人。
“我们不能再等了。”苏婉说,“‘灰域’已经不再是数据库,也不是行动计划。它是一种基因,一种文化抗体。我们要让它长进民族的记忆细胞里。”
她宣布启动“种子行动”:每位成员必须至少培养两名接班人,传授一套完整的历史记忆编码体系,形式不限??可以是棋谱、菜谱、剪纸花样、甚至是bedtimestory的节奏模式。
“不要追求规模,只要求精度。就像播种,不在乎撒了多少,而在乎有多少能活下来。”
会议结束时,众人依次起身,用手语打出同一句话:“我们在听,我们在传,我们还在。”
十一月中旬,一股更强的审查风暴席卷全国。教育部下发文件,严禁中小学开展“非指定主题”的课外阅读活动。多地出现“清书行动”,个别家庭因收藏旧版教材被约谈。
但与此同时,一股反向浪潮悄然兴起。
成都一位小学语文老师在辞职声明中写道:“我无法继续教孩子们把谎言读得朗朗上口。所以我决定去做一名街头storyteller,在公园里给陌生人讲真实的故事。欢迎来找我,我会一直讲下去。”
杭州一群大学生自发组建“流动图书馆”,骑着改装三轮车穿梭于城乡结合部,车上挂着横幅:“有些书,不怕风吹雨打。”
更令人动容的是,在甘肃一个偏远山村,村民们集体出资重建了一座被拆除的村史馆。馆内陈列的并非文物,而是上百个录音笔,每一个都录有一位老人讲述的家族往事。门口立着一块木牌:
“这里没有标准答案,只有不肯遗忘的人。”
腊月初七,北京迎来最冷的一夜。
苏婉独自走在长安街边,脚步踩在积雪上发出咯吱声响。远处,人民英雄纪念碑静静矗立,披着银霜。她停下脚步,仰头望着那巍峨的轮廓,忽然轻声念出一段早已烂熟于心的文字??那是她在邓伦笔记本复印件上看到的最后一句话:
>“所谓英雄,未必是站在高台上振臂疾呼的人。
>更多时候,是那个在黑暗中坚持点亮蜡烛,
>明知会被吹灭,仍一次次划燃火柴的人。”
她掏出随身携带的小录音机,按下录制键,将自己的声音录了进去:“我是苏婉。2023年12月7日,晴,零下8度。今天我想说,我没有放弃。我也不会让别人放弃。”
然后,她将录音机轻轻放在纪念碑基座旁,转身离去。
第二天清晨,清洁工发现了这台机器。他好奇地按下播放键,听见了女人平静的声音。他没听懂全部含义,却被那份执着打动。他没有上交,而是带回家里,放进了孙子的书包。
一周后,那个小学生在班级晨会上分享了这段录音。班主任皱眉制止,说内容“不适合未成年人”。但已有十几个孩子默默记下了开头那句:“我是苏婉……”
而此刻,在云南怒江峡谷深处的一所小学里,孩子们正齐声唱着一首新学的歌:
>“风来了,云散了,
>山记得,河记得,
>妈妈讲过的故事,
>比石头还硬,比星子还多……”
歌声飘荡在群峰之间,久久不息。
有人听见了。
更多人,正在学会倾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