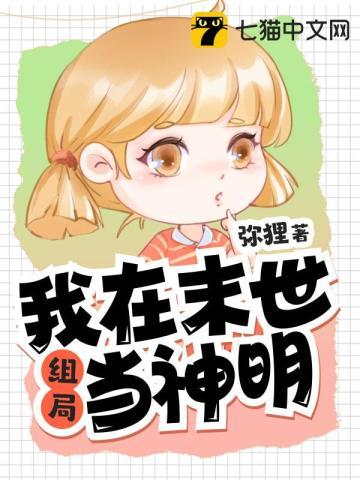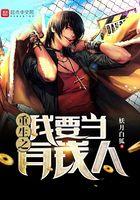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我要当大官 > 第二百三十一章 朕还能走到对岸吗(第1页)
第二百三十一章 朕还能走到对岸吗(第1页)
夜色深隆。
“大伴,你教教我,大燕还有救吗?”
紫禁城,乾清宫,烛火光亮,殿宇堂皇,崇宁帝头发凌乱,坐在冰凉的玉阶上,目光空洞地望向头顶那片幽深莫测的穹窿。
“陛下,您是天选之人,必。。。
夜色如墨,北京城的灯火在秋风中摇曳。苏婉坐在图书馆后院的老槐树下,耳机里循环播放着那封匿名来信中的《回音湖》。她已经听了七遍,每一遍都像被重新剖开一次记忆的伤口。那些声音??有的颤抖、有的坚定、有的几乎被风吞没??却在这片寂静里愈发清晰,仿佛从地底深处涌出的暗流,终于找到了出口。
她摘下耳机,抬头望向星空。银河低垂,像是谁把一卷写满字迹的羊皮纸撕碎后撒向天际。她忽然想起邓伦曾在若尔盖草原上说过的一句话:“真正的历史不会刻在碑上,它藏在人闭嘴时咬紧的牙关里。”
手机震动了一下。是李燕发来的短讯,仅一行字:“‘落叶归根’进入第三阶段,启动‘口述长城’计划。”
苏婉深吸一口气,指尖在屏幕上停顿片刻,然后回复:“明白。我这边已准备就绪。”
所谓“口述长城”,是他们最后的防线,也是最原始的反击。当所有电子通道都被封锁,当AI监控系统能预测一句话背后的百年隐喻,他们便退回到语言诞生之初??口耳相传。不依赖任何设备,不留下任何痕迹,只靠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讲述,将那些被抹去的名字、被烧毁的日记、被篡改的真相,一段段背下来,传下去。
这不是技术战,而是人性战。
第二天清晨,苏婉照例来到社区图书馆。孩子们陆续到来,围坐在地毯上,眼睛亮晶晶地等着她的故事会。她今天讲的是《石头记》,但不是曹雪芹的那一本,而是一个全新的版本??
“从前有座山,山上有一块会流泪的石头。没人知道它为什么哭,直到一个瞎眼老人路过,伸手摸了摸它的纹路,突然说:‘你记得的事,太多了。’原来这块石头曾是一面墙,墙上写满了名字。后来墙塌了,人们把砖头搬走,用来盖房子、铺路、砌猪圈。可每当下雨,那些砖缝里就会渗出黑水,像墨汁一样,顺着地面流淌,汇成一条小河。有个孩子蹲在河边,看见水里浮着字,他不认识,但他记住了形状。等他长大,成了老师,就把这些形状画给学生看,说:‘这是你们祖辈的声音。’”
孩子们听得入神。一个小男孩举手问:“那现在还能找到那条河吗?”
苏婉轻声说:“能。只要你愿意听,它就在你心里流。”
课后,几位家长留下来聊天。一位中年妇女犹豫了一会儿,低声问:“苏老师,您……是不是认识一位叫陈志远的教授?他在八十年代教过语文,后来……没了消息。”
苏婉心头一震。这个名字她太熟悉了??“灰域”早期联络网的创建者之一,1989年春在北京师范大学做完一场关于“民间叙事权力”的讲座后失踪,官方通报称其“精神失常,自行离校”,尸体三年后在永定河下游被打捞上来,口袋里塞着半页烧焦的手稿。
她看着这位妇女,缓缓点头:“他是我导师的朋友。”
妇女的眼眶红了。“我是他学生。这些年我一直记得他最后一堂课说的话:‘如果有一天课本里的故事全变了,别急着相信新版本。去找老人,找童谣,找戏台上的唱词,真相往往躲在最不起眼的地方。’我一直不明白,现在好像懂了。”
苏婉握住她的手,没有说话,只是轻轻点了点头。
当晚,她在家中整理资料,将《回音湖》音频拆解成十二个声部,逐一比对频率波形。惊人的是,在江南评弹那段“图书馆关门三个月”的尾音中,竟隐藏着一段极微弱的哼唱旋律??正是三十年前某位右派诗人狱中创作的《铁窗谣》副歌部分。而这首歌从未发表,仅有两名幸存者口述流传。
她立刻联系广西的技术组,要求用神经网络模型反向推演这段旋律的原始歌词。结果出来时已是凌晨三点:
>“锁得住门,锁不住风;
>烧得掉纸,烧不掉梦。
>我的名字死了,可我的影子还在走路,
>它穿过雪原,爬上屋檐,落在孩子的课本第一页。”
苏婉盯着屏幕,泪水无声滑落。
三天后,她启程前往山西平遥。根据最新情报,当地一座废弃戏台的地砖下,可能埋藏着1974年“批林批孔”运动期间被秘密销毁的民间文献残片。这处戏台曾是晋中地区最大的露天剧场,每逢庙会,万人空巷。而据一位临终老艺人的回忆录记载,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借排演古装戏之名,在台词中植入真实历史事件的隐语。
抵达平遥当晚,她以民俗调研名义住进一家老客栈,见到了接头人??一位六十多岁的退休语文教师老周。他鬓发斑白,手指因常年握笔而微微变形。
“我知道你要找什么。”老周一进门就说,“但我得先问你一个问题:你敢不敢让下一代活成‘异端’?”
苏婉怔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