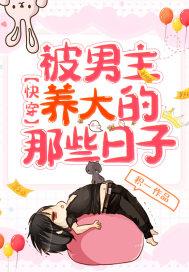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我要当大官 > 第二百二十六章 子弹日产量(第2页)
第二百二十六章 子弹日产量(第2页)
“那就赌一把。”李燕望着她,“你说过,你相信我不会放弃。那现在,请你也别放弃。”
苏婉久久不语,指尖轻轻抚过桌面,像是在触摸某种看不见的命运线。良久,她抬起头,眼中竟有一丝决绝的光:“好。我配合你。但我有个条件??我们必须留下证据链。”
“什么意思?”
“每一次违规操作,都要记录下来。”她说,“谁下的令,谁执行的掩盖,谁提供了虚假报告。这些信息也要加密存入‘灰域’,设定百年解密期。将来的人不仅要听到被封存的声音,还要知道是谁让它沉默。”
李燕怔住,随即缓缓点头:“这才是真正的存档。”
当天下午,一份名为《伊宁市教育史口述片段(节选)》的材料被正式提交至监管部门。其中仅保留了五段温和回忆:一位老师讲述如何用粉笔头教孩子写汉字,另一位回忆学生送来的野花摆在讲台上的情景……情感模型显示其情绪基调为“怀旧与温情”,顺利通过审核。
与此同时,在无人知晓的地下服务器群中,一段长达2分钟的完整录音悄然归档,编号:GRAY-XJ-1976-001。附注写道:
>“本录音因涉及敏感历史表述,依据内部决议予以暂存。
>存档日期:2025年2月3日
>预计解密时间:2100年1月1日零时整
>保管密钥持有者:李燕、苏婉、邓伦
>特别说明:本次归档行为未经官方授权,属个人伦理抉择。若未来因此追责,请将责任集中于本人??李燕。”
深夜,李燕独自驾车驶出城区,前往郊外一处废弃的数据中继站。这里原是上世纪电信系统的备用节点,后来荒废,却被“忆”项目秘密改造为离线备份点。他将一张微型固态硬盘嵌入墙体夹层,再用混凝土封死。那里藏着另一份拷贝,以及一段视频日记。
画面里,他穿着旧夹克,背景是斑驳的砖墙。
“如果有一天你们看到这个,说明我们失败了。”他说,“或者,说明你们终于成功了。我不知道那时的世界是否还能容忍真实,但我想告诉你们:我们试过。我们怕过,也逃过,但我们终究没有烧掉那些声音。也许你们会觉得我们懦弱,不敢公开,可我们也曾挣扎,在规则的缝隙里种下种子。请不要审判过去的人,因为他们手中的火种,本就不该由他们来点亮。”
他顿了顿,声音低了下来:“我只是希望,当你听见那位老师念出同伴名字的时候,能替我喊一声??我听见了。”
三日后,民政部发布新规,宣布将“临终语音采集”纳入全国殡葬服务标准化试点。消息传来,李燕正在云南回访一位参与“家音课”的彝族奶奶。老人拉着他的手,用方言说:“我现在每天吃饭前都要对着录音机说一遍菜单,等孙子长大,就能知道奶奶爱吃什么了。”
他笑着点头,眼眶却湿了。
返程途中,手机收到一条匿名短信,只有一个链接。他犹豫片刻,点开,是一段模糊的监控录像:两名穿黑衣的男子进入项目总部大楼B区地下室,撬开一台编号为DS-09的服务器机柜,取出一块硬盘后迅速离开。时间戳显示为两天前凌晨三点十七分。
李燕的心猛地一沉。
他立刻拨通苏婉电话:“‘灰域’主库有没有异地镜像?”
“有,但……”她声音颤抖,“只有我们三人知道访问路径。除非……有人背叛。”
“不。”李燕盯着窗外飞逝的山影,“不是背叛,是渗透。他们已经动手了。”
他想起最近几次会议都有陌生面孔旁听,想起安保系统莫名升级后台权限,想起某次数据传输日志出现无法解释的外联记录……
一切早有预兆。
当晚,他召集邓伦和苏婉召开紧急密会。地点选在乌鲁木齐一家老旧书店的地下室,那里曾是地下党印刷传单的秘密据点,如今成了民间口述史爱好者的聚会地。
三人围坐一圈,墙上挂着一幅手绘地图,标记着全国七处离线存储备份点。
“我们必须转移核心档案。”邓伦说,“不能再依赖单一系统。”
“问题是,”苏婉苦笑,“我们现在连谁可信都不知道。技术组有十二人接触过‘灰域’接口,运维团队另有八人掌握物理访问权限。”
“那就换方式。”李燕突然说,“既然他们能抓硬件,我们就把声音变成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