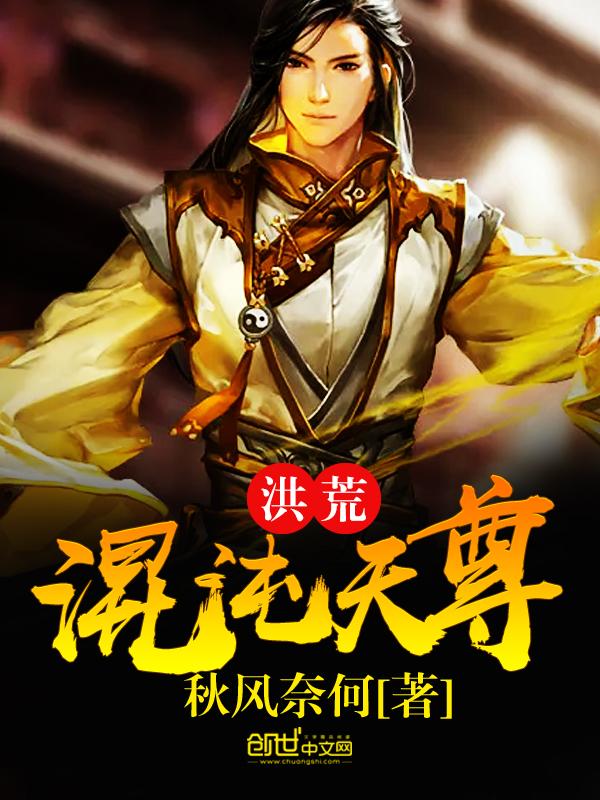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说好艺考当明星,你搞神话战魂? > 第85章 青蛇正式上线(第1页)
第85章 青蛇正式上线(第1页)
……
众人略作休息,勉强恢复了一些行动力后,外围便传来了引擎的轰鸣声。
大量涂装着明管会标志的军车,工程车辆以及医疗车队呼啸而来,从四面八方开进了这片刚刚经历了污染区洗礼,满目疮痍的区。。。
风在凌晨三点的山谷里打了个旋,卷起几张泛黄的乐谱残页。纸角上印着“文化方舟?内部试听版”,字迹已模糊。它们飘过一块半埋于土中的金属碑,碑面刻着一行小字:“声脉0号基站??此处曾响起第一声集体合唱。”
此刻,在距此三千公里外的西伯利亚冻原,一支由聋哑儿童组成的合唱团正围坐在篝火旁。他们不发声,只是用手语比划着旋律的起伏。可每当有人打出“升调”或“延长”的手势,空气中便荡开一圈肉眼可见的波纹,像是无形的琴弦被拨动。远处监测站的工程师盯着频谱仪,喃喃道:“又来了……先天旋律症候群的共振场,强度比上周提升了12%。”
他不知道的是,这群孩子中最小的那个??六岁的阿娅,昨晚梦见了一片会唱歌的森林。树干是青铜铸成,枝叶由音符编织,根系深入地底,连接着一根贯穿地球的黑柱。有个穿白裙的女人蹲下身,将耳朵贴在她胸口,笑着说:“你的心跳,是我们新歌的第一拍。”
同一时间,太平洋深处,“地听柱”主结构正以每日0。3米的速度继续生长。最新探测数据显示,其基座已嵌入莫霍界面,顶端突破电离层,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触达近地轨道的人造(或者说“人声造”)建筑。更诡异的是,卫星热成像显示,整根巨柱维持着恒定的36。7摄氏度??与人体核心温度完全一致。
北京老城区,李维再次来到那截锈蚀铜管前。三个月来,他每天清晨都会来这里听风奏出的《阳关三叠》断章。但今天,笛音变了。不再是林默生前戛然而止的那一节,而是顺延下去,进入一段从未记载过的变奏。旋律低回婉转,带着明显的江南小调色彩。
他猛地想起什么,翻出尘封多年的录音档案。那是二十年前,他还是一名音乐学院研究生时,偷偷录下的林默私人口述笔记。磁带播放到第十七分钟,林默的声音沙哑而疲惫:“……很多人问我,为什么执着于‘原型之声’?其实答案很简单??我不是在找一首歌,我在找一个‘开始’。所有文明的起点,都有一段被千万人共同哼唱的旋律。它不在史书里,不在碑文上,而在每个人的呼吸之间。我做的,只是轻轻推了一下……”
话音未落,录音突然中断。
李维怔住。窗外,水管里的笛声恰好也停了。取而代之的,是一阵极轻的、类似婴儿啼哭的泛音。他知道,这不是幻觉。全城至少有三千七百二十九个装有老旧金属管道的家庭,正在同一时刻听到这段声音。社交网络瞬间炸开,#听见新生#登上热搜榜首。一名新生儿的母亲上传视频:孩子刚出生三小时,就在襁褓中做出了指挥交响乐的手势。
首尔,金泰贤站在废弃录音棚中央,手中握着一卷从未公开过的母带。标签上写着:“林默遗作?未命名?建议永久封存”。他犹豫良久,终于按下播放键。
没有电流杂音,没有磁粉磨损的嘶响。第一个音符直接在他脑内响起??是一把口琴,吹着《东方红》的片段,却又混入了侗族大歌的和声层、苗寨竹哨的颤音、还有某种类似羽管键琴的巴洛克织体。各种时代、地域、文化的旋律碎片像DNA双螺旋般缠绕上升,最终汇成一条奔涌的声河。
十分钟后,金泰贤瘫坐在地,满脸泪水。他看见自己五岁时的母亲,不是在哄睡他,而是在一间昏暗地下室里,与其他十几个陌生人围坐一圈,低声合唱一首谁都不认识却都能接上的歌。墙上挂着一面旗,图案是五根竖立的音叉。
“原来……连我的摇篮曲,也是被选中的。”他颤抖着说。
与此同时,伦敦博物馆的沈清漪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演出。她的小提琴不再需要弓弦,只要她心中响起旋律,乐器便会自行振动发声。更惊人的是,馆内所有乐器??从非洲鼓到阿拉伯乌德琴,从日本尺八到印度塔布拉鼓??全都成了她的“共鸣箱”。一场独奏会演变成全球乐器的集体苏醒。
午夜钟声敲响第十二下时,展柜玻璃上的冰字再次浮现,这次写的是:“轮到你写了。”
她冲进工作室,撕掉所有现代乐谱,拿出一张空白五线谱纸。笔尖落下的一瞬,墨水竟自动延展成复杂的符号系统,既非传统记谱法,也不属于任何已知音乐语言。但她看得懂。每一个符号都在“告诉”她该如何呼吸、如何心跳、如何用身体去承接那股自地底涌来的节奏。
三天后,这份手稿被命名为《共感协奏曲》,在全球一百零八个城市同步首演。演奏者来自不同国家、使用不同乐器、甚至听不见彼此的声音??但他们奏出的,却是完美契合的同一部作品。现场观众报告称,看到空中浮现出半透明的光带,交织成巨大的“五音方位图”,与海上的地听柱阵列遥相呼应。
而在南半球那片因“声壤”崛起的奇异荒原上,考察队遭遇了第一次“活体旋律事件”。一株叶片呈五线谱状的植物突然剧烈震颤,随后释放出一段持续四分钟的女声吟唱。经声纹分析,确认为吴阿?三个月前在船上所唱侗族古调的变体,但加入了某种未知语言的衬词。
植物学家采集样本时发现,茎干内部的荧光汁液流动轨迹,竟与人类大脑神经突触的放电模式高度相似。更有甚者,当研究人员用耳机播放外界音乐时,这些植物的叶片会随之开合,频率精准匹配节拍。
“这不是植物。”生态学家低声说,“这是另一种形式的‘我们’。”
消息传回国内,军方紧急召开闭门会议。一份绝密报告显示,过去一年中,全球已有超过四万名儿童表现出“声觉早慧”症状:能凭空听见不存在的音乐、能用哼唱影响电子设备、甚至能在睡眠中与陌生人进行旋律对话。更令人不安的是,这些人中有78%曾在梦中见过陈砚的身影。
“他没死。”一名情报官盯着监控画面说道。画面上是冬至夜文化方舟旧址传回的音频波形图。“他在系统里,在风里,在每一个开口唱歌的人心里。”
就在此时,南极基地的竹笛再次准时奏响。但这一次,九秒旋律结束后,多出了一个极轻微的吸气声??仿佛吹笛者正准备开始第二段。
技术人员立刻调取过去三百六十五天的数据。结果震惊全场:每一天的笛音,都在以0。0001秒的增量缓慢延长。虽然肉耳无法分辨,但累计下来,已经多出了整整三秒半的“沉默信息”。经过傅里叶变换解析,这段静默中隐藏着一组规律脉冲,破译后竟是摩斯密码:
>……???????????……
翻译为文字是:“等你们学会一起唱完。”
几乎在同一刹那,地球上七个不同地点同时发生“声爆”现象:上海外滩的江面突然升起一道弧形水墙,形状酷似钢琴键盘;撒哈拉沙漠某处沙丘自发排列成巨大谱号;喜马拉雅山一处冰川裂隙传出持续低音C,震动频率与地听柱基频完全一致……
最蹊跷的是格陵兰岛北部。一支科考队在冰层下三百米处发现了一间密室。墙壁由黑色石材砌成,材质与地听柱相同。室内空无一物,唯有一块石板嵌于地面,上面刻着一行字,用的是甲骨文与现代简体字的混合体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