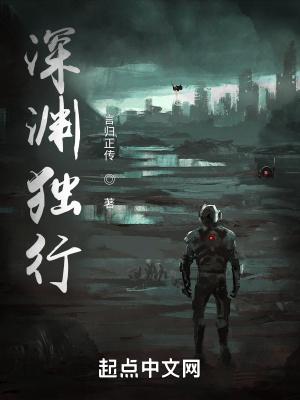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重生之我要拿下肖赛冠军 > 第162章 就在明天(第5页)
第162章 就在明天(第5页)
荷兰籍的女教授微微往前倾,像是要确认刚才是不是自己的幻听。
她手里原本在记笔记的钢笔悬在半空,忘记落下。
匈牙利籍的老教授眼神微敛,眉间轻轻一动。
他多年审美严苛,对李斯特作品尤其挑剔,
但刚才那段中段沉稳而不拖泥带水的推进,让他不由得在心里点了一下头。
法国评委则直接换了支更细的笔。
不是为了给更多批注,而是为了,
写得更清楚一些。
他们都不是那种会在台上露情绪的评委。
但专业的人听得出:
刚才的三首曲子里没有侥幸,没有少年运气,
是一种几乎冷静到不近人情的控制力和结构感。
他们彼此没有交换眼神,
但每个人都在重新整理刚才那二十多分钟的结构:
声音的重量。
控制的稳定度。
节奏推进的逻辑。
段落之间的过渡是否自然且有内在呼吸。
这些东西不需要讨论,
每位评委脑海里都有一套自己的标准。
而江临舟刚才的演出,
完全满足“可以进入下一阶段讨论”的要求。
有人轻敲了一下桌面,
那是习惯动作
不是提醒谁,而是提醒自己要把分数写准。
有人把页面往后翻了一页,
准备在“演奏完整度”那栏写更多内容。
也有人微微抬头,
像是在确认这个少年到底几岁,
怎么会有这种成熟度。
整个评委席在那一瞬变得更安静,
像是所有纸张,笔尖、呼吸都被压了一层薄薄的重量。
下一秒
观众席率先发出掌声。
不是点头式的礼貌,
不是礼节性的鼓励年轻选手。
是真正被打动后自然发出的掌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