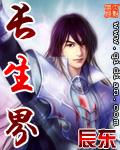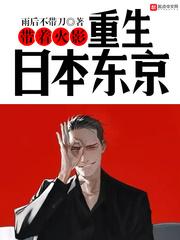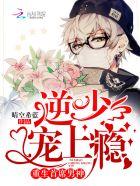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晋末芳华 > 第五百二十四章 绝不后退(第1页)
第五百二十四章 绝不后退(第1页)
苻登还在庆幸躲过了对手的杀招,正要拉动缰绳,拨转马头反击,却发现手不听使唤了。
他下意识想要扭过头去,这时候脖子处传来不适感,让他心生不妙的预感。
眼前清晰的景象开始变得模糊,触目所见,都。。。
雪停了,天光微亮时,小满起身梳洗。她将那只塑料风铃用红绳系好,挂在窗前最显眼的位置。阳光穿过薄雪折射进来,在铃身洒下一道七彩光斑,像极了当年塔克拉玛干夜空中的“心环”。她没再去看它是否晃动??她已学会不再追问声音从何而来,而是先问自己:我有没有准备好去听?
这一天是回音日的第九年。
联合国总部外的广场上,人们正搭建临时舞台。今年的主题是“未完成的对话”,邀请全球各地普通人提交他们想对逝者说的一句话。这些话语会被录入特制音频盒,由七国少年代表护送至塔克拉玛干遗址,在第七棺椁前集体播放。小满本被列为特邀嘉宾,但她婉拒了行程。她在信中写道:“真正的倾听,不在仪式之中,而在日常之隙。”
她选择留在北京,打开家中那台老旧录音机,开始录制新一期冥想音频。这一次,她没有加入鸟鸣或风声,只录下自己的呼吸,以及手指轻抚琴弦时那一瞬的震颤。“今天我们要练习的,不是如何说话,”她的声音低缓而沉静,“而是如何在别人说话之前,先安静下来。因为很多时候,对方真正想告诉你的,并不在言语里。”
录音结束,她照例把文件上传至共感档案库,附注一句:“致所有独自走过长夜的人。”然后关掉电脑,穿上棉衣出门。养老院的陈望舟已于半年前安详离世,临终前最后一句话仍是关于《心音引》:“第三段落……少了一个音。”没人知道那个音是什么,连小满也无法补全。但就在老人闭眼那一刻,世界各地的心音园铜铃齐鸣,持续整整三分钟,分秒不差??仿佛天地也为一位传承者的离去默哀。
小满如今常去一家社区图书馆做志愿者。那里有个小小的角落叫“静听区”,摆着几把椅子、一台老式留声机和一面镜子。来这里的多是孤独的老人、失业的年轻人、刚离婚的夫妻,或是失去孩子的父母。他们不说什么,只是坐着。有时小满会为他们弹一段即兴曲,更多时候,她只是陪着坐。
这天下午,一个穿灰夹克的男人走进来,坐到了最角落的位置。他约莫五十岁上下,鬓角斑白,眼神游移不定,右手始终插在口袋里,似乎藏着什么东西。小满注意到他的鞋底沾着黄泥,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徒步而来。
她没上前打扰,只是轻轻拨动琴弦,奏起《回音赋》的前奏。男人的身体微微一震,却没有抬头。
一曲终了,窗外飘起了细雨。男人终于开口,声音沙哑:“你就是林小满?”
“我是。”她点头。
“我找了你三年。”他说着,从口袋里抽出一只布包,层层打开,露出一枚残破的铜铃。铃舌断裂,表面锈迹斑斑,但内壁刻着一行极小的文字:“愿声渡苦海”。
小满瞳孔微缩。这不是普通的铃,也不是基金会配发的制式铜铃。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第一批“心音计划”实验者所持有的原型铃之一。全球仅存不到十枚,每一枚都代表着一段被遗忘的历史。
“你是……参与者?”她问。
男人苦笑:“我是第零号实验体。”
小满心头一震。所谓“第零号实验体”,并非正式编号,而是内部档案中对最早一批共感训练失败者的隐称。他们在1987年至1993年间接受过非公开神经调谐实验,试图通过特定频率刺激大脑颞叶,激发共感能力。结果多数人出现严重精神紊乱,甚至自杀。项目最终被封存,相关资料列为绝密。
“你怎么活下来的?”她低声问。
“因为我学会了假装听不见。”男人缓缓道,“可我也因此背负了一辈子的罪。”
原来他名叫周临川,曾是一名战地记者。1992年萨拉热窝围城期间,他奉命拍摄一组平民撤离画面。途中遭遇狙击手伏击,同行五人当场死亡,唯有他因耳疾发作躲在掩体后侥幸逃生。当时他戴着实验配发的铜铃,却在枪响瞬间本能地捂住耳朵,切断了与外界的声音连接。
“我听见了他们的惨叫,但我选择了屏蔽。”他闭上眼,“那一刻,我不是为了保命,而是害怕那种痛……会把我撕碎。”
此后三十年,他辗转各国,靠写作维生,却再未拿起录音设备。直到七年前,“第七共鸣事件”发生当晚,他梦见自己站在废墟中,五个亡魂围着他,无声张嘴。醒来时,枕边铜铃竟自行响起,持续十九秒??正是当年枪击持续的时间。
“我知道他们要我回来。”他说,“不是赎罪,而是完成一次真正的倾听。哪怕只是一次,我也必须听见他们最后的声音。”
小满沉默良久,起身取来昭华琴。她将琴置于两人之间,双手轻放于弦上。
“那你现在准备好了吗?”她问。
周临川颤抖着点头。
琴声起,低缓如潮汐退去。小满并未演奏任何已知曲目,而是依循直觉,让音符随对方呼吸起伏流动。渐渐地,周临川的手从口袋抽出,放在膝盖上,掌心朝天,仿佛在接受某种审判。
忽然,他喉间发出一声呜咽,继而化作哭嚎。泪水汹涌而出,身体剧烈抽搐,口中喃喃重复着几个名字:“阿米尔……丽莎……老吴……你们说得对,我一直都在听,我一直都听见了……对不起,我真的对不起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