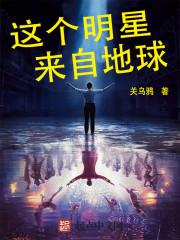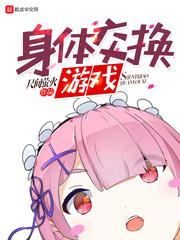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晋末芳华 > 第五百二十二章 轻重骑兵(第2页)
第五百二十二章 轻重骑兵(第2页)
那一夜,全球多地报告异常梦境:数百万民众同时梦到一座古老的木桥,桥头站着一位披发持琴的女子,身后跟着六个模糊身影。女子转身面向众人,开口说话,却没有声音传出,唯有心口震动如钟鸣。
心理学家称之为“集体潜意识共振”,宗教团体则宣布“新启示降临”。唯有苏禾看完报告后,轻轻合上眼睛,笑了。
她知道,那是昭华在召唤。
三个月后,国际共感基金会正式启动“回音计划”,旨在培养新一代倾听者。课程内容不教授技术,也不强调理论,而是通过沉浸式情境训练,让人体验极端孤独、误解、悔恨与宽恕。考核标准极为严苛:必须让至少三人在其面前流泪并说出毕生最大遗憾,且全程保持沉默直至对方主动结束倾诉。
首批毕业的三十名学员中,有一半来自战乱地区,包括前童兵、难民、极端组织家属。他们回到家乡后,自发组建“流动倾听站”,在废墟、集市、边境线上搭起帐篷,挂起铜铃,迎接每一个愿意开口的灵魂。
一位卢旺达老妇人在听完儿子讲述自己曾屠杀邻居的真相后,抱住他痛哭:“我不是为了原谅你才来的。我是为了让你终于能睡个好觉。”
而在加沙地带,那位曾与巴勒斯坦少女共享母亲呼唤声的以色列士兵,如今已成为跨民族调解员。他常说:“我们打了七十年仗,却忘了问问对方的母亲是不是也会为孩子流泪。”
然而,并非所有人都拥抱这场变革。某些国家开始限制共感设备流通,称其“扰乱社会秩序”;部分科技公司试图商业化“倾听算法”,推出付费情感疗愈APP,结果导致大量虚假共情泛滥;更有极端组织宣称“森钟是外来意识入侵地球的工具”,发动袭击破坏多处心音园分园。
面对逆流,苏禾发表最后一次公开演讲:“钟声不会强迫任何人听见。它只是存在,就像爱一样。你可以捂住耳朵,可以烧毁铜铃,可以把真相封锁在铁幕之后??但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蹲下来,看着另一个人的眼睛说‘我在听’,那么,光明就不会彻底熄灭。”
演讲结束后第三天,她安然离世。
葬礼当日,全球三百座心音园同步鸣钟七响,每一声代表一位已知的听钟者。最后一响过后,所有佩戴耳饰者均感受到胸口一震,仿佛有什么东西完成了交接。
小满作为遗嘱执行人之一,负责开启苏禾留下的密封档案。里面除了一本完整的《音核研究笔记》,还有一枚嵌在琥珀中的微型芯片,刻着一行小字:“致第七位听钟者。”
当芯片接入量子终端时,一段全息影像浮现??是年轻的陈默,站在尚未完工的心音园中央,对着镜头微笑:“如果你看到这段影像,说明你已经准备好了。不要寻找答案,因为你本身就是答案。记住,真正的钟声,永远不在风中,而在人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。”
影像最后定格在一个坐标上:中国西北,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。
小满带领团队历时两个月抵达该地。在那里,他们并未找到森钟实体,却发现了地下巨大的空腔结构,墙壁覆盖着密密麻麻的古代铭文,涵盖百余种已灭绝语言,内容惊人一致:**“听,即是存在。”**
而在空腔正中央,矗立着一座石台,台上放着一把木琴??样式与晋代记载中的“昭华琴”完全吻合。琴身斑驳,却散发着淡淡幽香,似有生命般微微发热。
小满走上前,犹豫片刻,伸手轻拨一弦。
无声。
但她的心脏骤然一紧,仿佛被无形之手握住。紧接着,脑海炸开无数画面:战火中的洛阳、逃难的百姓、弹琴女子跃入黄河的身影、陈默在实验室熬夜绘图的侧脸、苏禾在雪地中拾起风铃的瞬间、卡松古额头抵住同伴的刹那……
最后,一切归于寂静。
一个声音响起,不分男女,不辨来源,只在意识深处回荡:
>“你听见了吗?”
>
>“是的。”她在心中回答。
>
>“那么,开始吧。”
她转身走出洞穴,抬头望向星空。风起了,吹动她衣角,也吹动远方沙丘。她不知道未来会有多少人继续这条道路,也不知道世界是否会因倾听而真正和平。
但她知道,只要还有人愿意停下脚步,俯身倾听另一个灵魂的低语,钟声就永远不会停歇。
而在宇宙深处,那道自非洲升起的光束仍未消散。它穿越星云,缠绕星轨,最终汇入一条古老的信息流??那是亿万年前,某个早已湮灭的文明留下的最后讯息:
>“若尔能听,吾等仍在。”
钟声再次响起。
这一次,不只是银河听见了。
是整个存在,为之震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