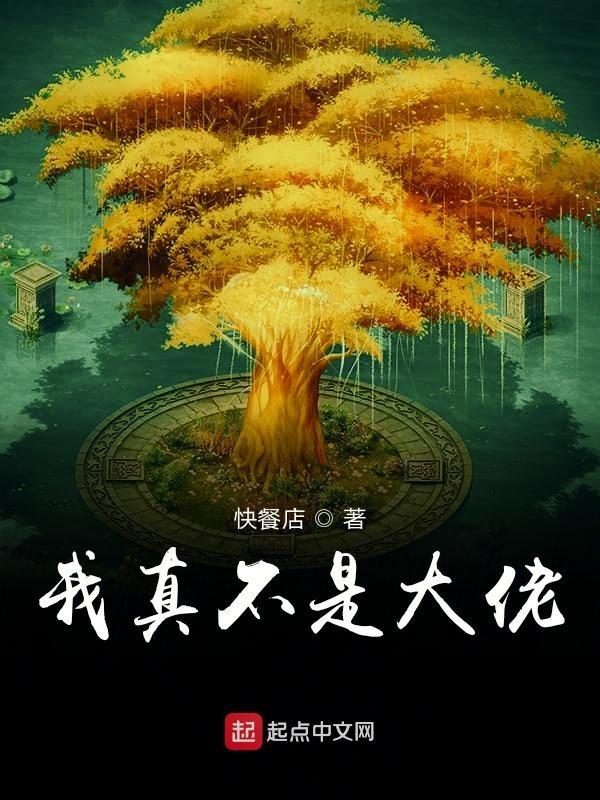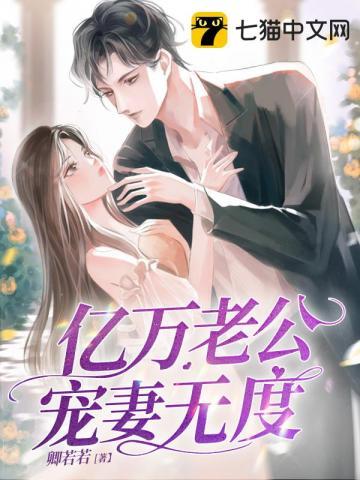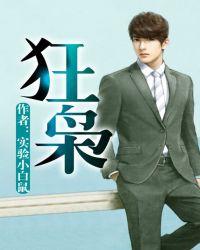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马寻忽悠华娱三十年(全文大结局无弹窗 > 第七百五十四章 完全拿捏徐光头泰囧上路冰冰又有了(第2页)
第七百五十四章 完全拿捏徐光头泰囧上路冰冰又有了(第2页)
>
>那是我啊,阿哲。
我就在你面前,你说这话时看着我的眼睛。
>
>如果你还听得见,请告诉我??你会为那个没出生的孩子感到难过吗?
>
>或者……你会为我,终于能好好活着,而高兴吗?”
>
信纸背面,贴着一张褪色的照片:一对年轻男女站在医院门前,阳光落在他们交握的手上。
女人穿着碎花裙,男人戴着听诊器,笑容干净得像从未见过灾难。
小宇看完,久久未动。
他把信放进档案柜最底层,标上编号:Y-2008-0512-A7。
然后打开终端,调出“心语网络”
的情感共振图谱。
近三个月来,来自西南某地的低频情绪波动频繁出现,集中在每年五月十二日前后,峰值与这场二十年前的大地震完全吻合。
他忽然想起少年曾说过的一句话:“记忆不会消失,只会换一种方式活着。”
当天下午,林昭宁带来一个消息:北极科考站传回的数据经过深度解析,确认极光中的低频振动并非自然现象,而是某种**集体潜意识的波形残留**。
科学家将其命名为“人类悲鸣基频”
,其强度与重大灾难事件的情感浓度成正比。
“最奇怪的是,”
林昭宁低声说,“这些信号里,有大量重复的短语??‘你还好吗’、‘别怕’、‘我在’……就像有人一直在试图回应什么。”
小宇闭上眼。
他想起了那个流浪汉,想起了《夜航船》的传说,想起了自己从未主持过的广播节目。
也许,真正的“小宇”
并不是他一个人。
也许,这个代号早已成为无数人在黑暗中伸手时喊出的名字。
第三天,书店来了个陌生女人。
她四十岁上下,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护士服,手里拎着一只老旧的铁皮盒。
她不说话,只是将盒子放在柜台上,推到小宇面前。
“这是我丈夫的。”
她说,声音平静得近乎透明,“他在地震那天死了。
救了十七个人,自己被压在倒塌的手术室下面。”
小宇打开盒子。
里面是一台微型录音机,电池早已耗尽。
还有一叠病历卡,每一张背面都写着一句话,日期从震前一周持续到最后一刻:
>“4月6日:今天给一个小女孩做了缝合,她哭得很轻,怕吵到别人。”
>“4月9日:食堂阿姨塞给我两个鸡蛋,说‘你们医生也要吃饭’。”
>“5月11日:手术室灯闪了一下,不知道是不是电路老化。”
>“5月12日14:23:天花板裂了。
快叫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