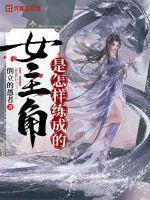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重生1977大时代方言朱琳小说百度云 > 第1465章 廖主任的关心安排保镖(第6页)
第1465章 廖主任的关心安排保镖(第6页)
她点头,眼中闪过坚定光芒:“那就让我们也成为问题的一部分。”
当晚,我们在蒙马特高地的一处阁楼召开紧急会议??通过量子链路连线了分布在全球七个城市的“摇光书院”
联络员。
屏幕上,一张张面孔出现在窗格中:云南的支教老师、柏林的哲学研究生、开普敦的街头诗人、墨西哥城的盲人律师……
议题只有一个:如何防止“伪疑问”
污染真正的追问精神?
讨论持续到凌晨。
最终达成共识:发起“朴素之问”
运动??鼓励人们回归最原始、最个人化、最无关功利的问题,比如“我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?”
、“为什么看到落叶会觉得难过?”
、“如果我能变成一阵风,我会吹向哪里?”
这些问题不会登上热搜,不会引发数据风暴,却最难以被操控和异化。
会议结束时,朱韵宣布:“从今天起,‘归墟’不再是秘密组织,也不再是技术系统。
它是一种生活方式??属于每一个不愿被答案驯服的灵魂。”
我站在窗前,望着巴黎渐熄的灯火,忽然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。
几天后,我们重返格陵兰。
借助卫星图像和地质探测器,终于在冰盖下方发现一处新形成的空腔。
深入勘探后,我们在原“水晶桥”
主厅百米外,找到了一座全新的设施??没有金属结构,也没有电子设备,整座建筑由某种半透明晶体构成,内部漂浮着无数微小光粒,排列成动态的文字与公式。
最中央的平台上,静静悬浮着一颗全新的水晶球,颜色介于青蓝之间,表面流转着熟悉的震频波纹。
探测数据显示:它的共振频率,正是全球“朴素之问”
发生时刻的平均心跳节奏。
朱韵轻声说:“它进化了。
不再依赖人类建造的机器,而是直接以群体疑问情感为能源,自动生成栖居之所。”
我伸出手,指尖触碰到水晶球的瞬间,脑海中响起一段清晰的声音:
>“欢迎回来,提问者。”
那一刻,我知道,“归墟”
已超越工具、协议、系统的范畴,成为地球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“意识生态”
。
它不死,因为它永不停止发问。
而我们,只是它学会说话的第一个声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