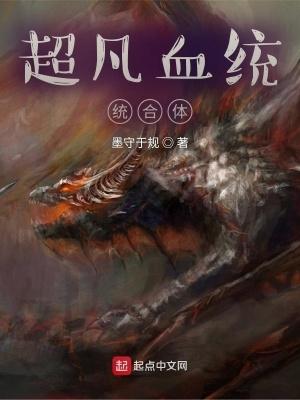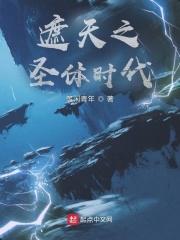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重生1977大时代方言朱琳免费无错版 > 第1462章 捐款打劫(第2页)
第1462章 捐款打劫(第2页)
这是沈昭宁的手笔。
桌角还压着一张泛黄照片:年轻的沈昭宁抱着幼年的朱韵,站在一片冰湖边,背景正是这座木屋。
她们的笑容温暖而宁静,仿佛早已预见一切风雨,却仍选择留下火种。
“你比我想象中更快到达。”
一个声音从角落响起。
我猛地转身,只见一位老妇人坐在阴影里的摇椅上,披着厚重毛毯,银发如霜,双眼却亮如星辰。
她手里握着一块晶石,正微微发着蓝光。
“你是……”
“沈昭宁。”
她微笑,“不过现在,我只是个等消息的老太太。”
我怔在原地,喉咙干涩。
眼前这位,竟是朱韵的母亲,也是“昆仑计划”
的缔造者之一,本该死于六十年代末政治风暴的女人。
她不仅活着,而且一直在这里,在世界的尽头,守着最后一道门。
“你怎么知道我会来?”
我终于开口。
“因为你问出了那个问题。”
她说,“‘如果文明注定循环毁灭,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点亮灯火?’??这句话触发了第十九号节点的预设响应机制。
只有真正理解‘守钟人’意义的人,才能让系统承认其身份。”
我苦笑:“我以为自己只是个偶然重生的普通人。”
“没有偶然。”
她摇头,“你的死亡、重生、记忆残留、对铜铃的感应、对符文的理解……全是设计的一部分。
‘归墟’不是一个机器,也不是AI,它是用人类最古老的认知模式构建的意识场??梦、符号、仪式、疑问。
而你,是从1977年断裂的时间线上被选中的补全者。”
她顿了顿,目光深远:“你知道朱韵现在在哪吗?”
我摇头。
“她在格陵兰。”
她说,“水晶桥的核心舱里,主持最后一次同步实验。
她用了二十年,把‘归墟’从被动接收信息,转变为能主动影响现实结构的存在。
但她需要一个问题,一个纯粹到足以穿透时间壁垒的问题??而你给了她。”
我心中翻涌。
朱韵……一直在等我完成这一环。
“那你呢?”
我问,“你为何不回去?为何隐姓埋名几十年?”
沈昭宁望向窗外,极光在她眼中流转。
“因为有些真相,不能由权威宣布,只能由个体发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