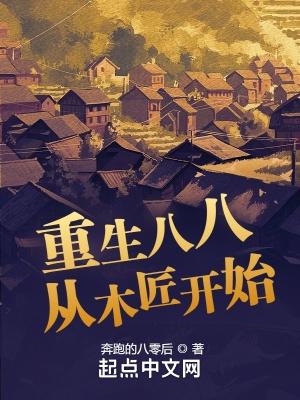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致我的少年 > 5060(第18页)
5060(第18页)
孔净整个人像熟透了的水蜜桃,粉薄皮下清甜饱满。
“如果这叫糊弄,你可以不要。”
她被体温烘得发红的手掌贴着陈端的后颈。
以前看电影时不懂,还以为是导演故意延拓时间,以此增加观众的窥探欲。
现在才渐渐明白,互相的身体探索、适当的气氛烘托是促使人体分泌大量多巴胺的必要阶段,人说到底追求的都是感官和精神体验。
正因为如此,只要没有真的获得,孔净吊在陈端面前的那根胡萝卜就永远令他垂涎。
他以为他尝到了,到头来只是嗅了下胡萝卜的香气、舔了下胡萝卜的汁水,到真正意义上的品嚼长路漫漫。
更毋宁说是餍足。
“你们学霸是不是都这样?”
陈端红着眼眶,唇齿压在皮肤里声音显得又闷又粗。
“哪样?”
“凡事都做个计划表,说好听点叫循序渐进,难听点就是吊足胃口,虚与委蛇。”
他后面跟了个脏字,然后在孔净允许的地方用力吻咬。
“……随你、怎么说。”
孔净吞吐困难,两手反过来紧紧扣住轻轻桌沿。
后来陈端去了趟浴室,花洒一直开着,他在里面待了很久。
夜里,他们紧缩在一张单人床上,盖着一床被子。
孔净的头发太长太厚,陈端怕压到扯痛她,垫在她脖子下当枕头的那只手折过来,配合着另一只手帮她用皮筋挽了下。
发丝在指间滑过,像游鱼一样根本抓不住。
陈端忽然反应过来,“孔净,你是不是给自己留着后路啊?”
孔净侧躺着后背抵着他滚烫的身躯,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。
过了几秒,她温吞地回了句,“你说什么?”
“没什么,睡吧。”
陈端把她抱紧了,堵死在她身后。
除夕这天,阖家团圆的日子,无论怎么样都是要吃顿团圆饭的。
孔净早早起来,陈端陪她一起去市场买菜。
人很多,冷清的空气也被渲染得热烈,隐约可以闻见烟花爆竹燃放过的味道。孔净两手揣兜里,穿梭在一个个摊贩面前,她负责挑选和讲价,陈端负责出力拎东西。
陈端把孔净和一兜子菜送回出租屋,之后去接孔大勇。
拖拖拉拉到了下午一点多才吃上午饭。
日子都烂糟到这份上了,孔大勇还不忘自带酒水,叼着一根烟屁股进门,在白雾中眯眼梭巡一圈。
“房子这么小……”他脑袋被酒精毒害,反应过分慢,坐下来嚼了一把油炸花生,才发现不对劲,“一张床怎么睡?”
“陈端晚上打地铺。平时我们都住校,只有放假才过来。”
孔净知道陈端在看自己,但她没抬眼,语气很平静。
孔大勇好糊弄,只顾着往嘴里灌酒塞菜,陈端面前一只酒杯,陪他喝。
高浓度的劣质白酒,一瓶见底,孔大勇约莫微醺了,就开始滔滔不绝了。
当然还是老生常谈,讲讲过往荣光,再控诉如今时运不济,话锋一转,向陈端和孔净开炮。
他不承认李贤梅的离家出走跟自己有任何关系,把所有责任都归咎于孔净不听话、陈端不喊她妈。
最后他要揍陈端,因为想起被那条街的娱乐场所拒之门外以及进口摩托的事了。
摇摇晃晃,站起来都走不成直线,饭桌倒先被他掀翻了,菜碟、酒瓶哗啦啦铺得满地都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