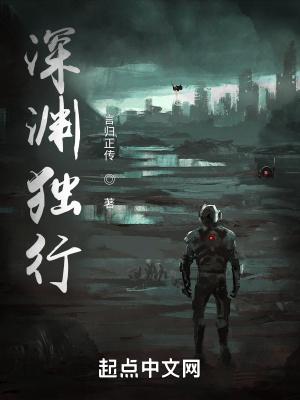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李珞应禅溪重燃青葱时代免费阅读全文 > 第878章 小王子与玫瑰(第3页)
第878章 小王子与玫瑰(第3页)
她立刻调取系统记录,发现这个少年名叫周岩,十二岁那年失去双亲,如今十六岁,辍学半年,居无定所,靠打零工和网吧过夜维生。
“必须介入。”
她拨通心理援助中心的电话,“紧急等级A,需要临时安置和持续干预。”
挂断电话,她又翻开《倾听手记》,在最新一页写下:
>“今日新增危机个案一例。
周岩,16岁。
他曾以为自己是灾祸本身,直到有人告诉他:火光吞噬的不是你,而是时间来不及修补的遗憾。
>我们接住了他坠落的瞬间。
接下来,要教他如何站立。”
傍晚时分,陈默从青海发来视频请求。
画面接通后,他身后是一排破旧课桌,十几个学生围坐在一台笔记本电脑前,神情紧张又期待。
“袁姐,”
陈默笑着说,“他们有几个问题,想直接问你。”
镜头切换,一个扎马尾的女孩怯生生举起手:“袁老师,我……我也想给别人写信。
可是我没钱买邮票,也没人告诉我该写给谁……”
袁婉青温柔回应:“我们有‘信使接力计划’。
只要你愿意写,就会有人替你寄出,也会有人回你。
信不需要完美,只需要真实。”
另一个男生接过话筒:“如果我说我很恨我爸,因为他打了我妈十年……这也能说吗?”
“当然能。”
袁婉青声音坚定,“愤怒也是一种声音,它值得被听见,而不是被压抑。
我们可以帮你联系法律援助,也可以安排心理咨询。”
孩子们一个个发言,有的问如何应对校园霸凌,有的说自己梦想当医生却被嘲笑“穷人家的孩子别做梦”
。
袁婉青一一回应,语气平缓却有力。
屏幕那端,陈默静静站着,眼里闪着微光。
视频结束前,最后一个小女孩低声说:“我从来没跟人说过这些……但刚才,我觉得心里轻松了一点。”
“那就够了。”
袁婉青微笑,“有时候,改变不是轰轰烈烈的拯救,而是某一天,你终于敢对自己说:我不是错的。”
当晚,袁婉青独自坐在办公室,重播这段视频。
她注意到,每当有孩子开口说话,陈默都会轻轻点头,动作细微却充满肯定。
她忽然明白,真正的教育,从来不是灌输答案,而是守护提问的权利。
凌晨一点,她正准备关机,邮箱提示音响起。
附件是一份PDF文档,标题为《致海风邮局全体志愿者的一封公开信》,署名“一群正在学习倾听的人”
。
她点开阅读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