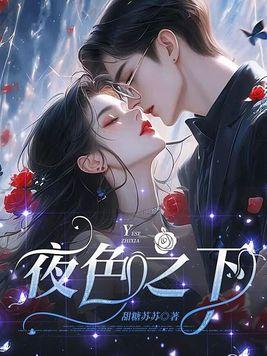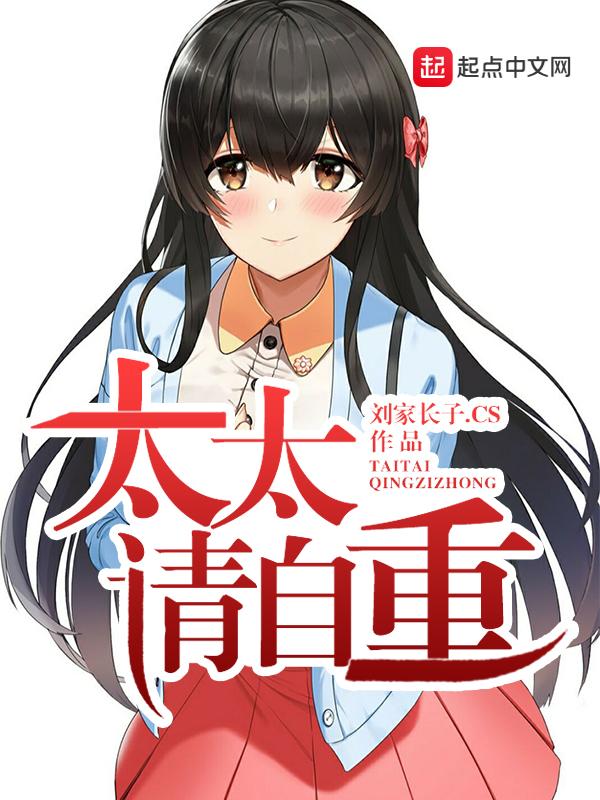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大明兽医,开局给朱标续命 > 179 被座师背刺了(第1页)
179 被座师背刺了(第1页)
天光大亮,晨光透过窗户纸洒进书房,光柱里满是细碎的尘埃。
许克生从梦中醒来,
脑袋还有些昏沉,却比昨夜清爽了不少。
看着外面明亮的晨光,许克生叹了口气,
“这是第一次起晚了。还。。。
夜色如墨,钟山深处的松林间雾气弥漫。老梅树下,一块青石碑静静矗立,上面刻着“仁心所系,万民同念”八字,字迹清瘦却有力,是清扬亲笔所书。每逢月圆之夜,总有村民远远望见石前似有微光闪烁,仿佛有人影伫立不语。他们不说破,只在家中对孩子道:“那是太子爷还在看顾咱们。”
这一夜,恰逢中秋。
新生书院内灯火通明,礼堂中摆满了桌案,每张桌上都放着一碗热腾腾的腊八粥??虽非腊月,但这是朱标生前最爱的食物,也是他定下的“百姓日”习俗:每年此日,全国义学、医馆、驿站皆免费供粥一日,不论身份贵贱,皆可入座共食。
孩子们穿着新裁的蓝布衫,围坐一堂,捧碗啜饮。阿福也被接来,由一名女学生牵着手引路。他摸着碗沿,忽然咧嘴笑了:“好烫。”
“烫才暖啊。”小女孩说,“我娘讲,太子爷说人活着,就得有点热乎气儿。”
阿福点点头,小口小口地喝起来,脸上泛起红晕。
清扬站在廊下,望着这一幕,手中握着一封刚送到的信。信封上无署名,只有火漆印是一枚梅花图案??那是她与陈启明十年前约定的暗记。她拆开一看,竟是漳州南靖县来的消息:
>“归命道残余据点已清。昨夜大雨冲塌山崖,露出一座地下石室,内藏铁棺三具,棺面刻‘奉紫衣尊者令,镇魂以护法统’字样。启明率军医入内勘察,发现棺中并非尸体,而是三名被药物麻痹多年之人,尚存气息。现已救醒二人,其一口述:当年被诱入道门时年仅十四,被告知‘舍身成神,庇佑全家’,实则沦为药引容器,每日抽取精血炼制‘阳德续命散’……”
信纸微微颤抖。清扬闭上眼,脑海中浮现出那些曾在地窟中挣扎哀嚎的身影。她记得朱标曾问她:“若有一天,我能用自己换千人活,该不该做?”
她当时答:“不该。因为你不是神,你是人。而每一个普通人,也都值得被救。”
如今,那场噩梦终于彻底揭开最后一层黑纱。
她将信收入袖中,转身走入厨房。灶火正旺,几位妇人正在蒸制月饼。一名老妪抬头笑道:“夫人,今年还是您教的素馅吧?莲蓉加枣泥,一点荤油都不沾。”
“太子清修一生,不爱奢华。”清扬轻声道,“他说过,最怕闻到肉腥味,因为小时候见灾民易子而食,从此再难下咽。”
众人默然片刻,反倒笑出声来。笑声里没有悲戚,只有一种历经苦难后的温厚。
“是啊,他连龙袍都没穿过几天。”
“可我们人人都穿上了新衣。”
“我家娃上学领的校服,比县太爷的官服还整齐哩!”
清扬也笑了。她拿起一把木勺,亲自为每一锅粥添上一撮盐??这是朱标定下的规矩:“甜食悦口,咸食养命。百姓要过得踏实,就得知道生活不止有糖,也有苦和咸。”
子时将至,书院后院燃起百盏灯笼。学生们手执蜡烛,排成长队走向“遗志堂”。这座新建的厅堂不大,却庄严肃穆,四壁挂满信笺,皆为百姓写给朱标的书信。有的字迹稚嫩,有的潦草不堪,甚至还有用炭条画出的一幅全家福。
清扬缓步上前,在中央案台铺开一张宣纸,提笔蘸墨,开始书写《遗志堂序》。
>“夫人生天地之间,贵者非位,富者非财,而在其行能否照他人之路,其言能否醒迷途之心。太子朱标,未登九五,而德泽遍于九州;不执斧钺,而仁声动于四海。其所求者,非庙号谥美,非史册留名,唯愿天下少一饿殍,多一读书声耳。
>
>昔年疫起,冰蟾髓现,世人皆谓可延寿千年。彼时权贵争购,黄金万两不足惜。然太子下令封药,亲撰文书曰:‘此药未成,不得外流;若有伤亡,罪在我身。’直至三年后方准用于民间,首剂即投于灾区垂死幼童。今观之,非其不爱生,实不忍以一人之命,压万人之望。
>
>或问:何谓仁政?答曰: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失学,不让一位病人因穷断药,不让一句真话因惧沉默。此即仁政。”
>
>……
笔落之时,东方微白。
忽听得门外喧哗,一名快马信使滚鞍下马,高呼:“福建急报!陈大人在南靖掘出归命道总坛遗址,得秘册一部,题为《紫衣经解》,其中详载三十年来操控人心之术:借灾立神、以恐驭众、伪托天命、制造圣物……更有图示如何利用幻药与催眠,使人自认‘见神显灵’!现已抄录副本呈送国民医政司,并请旨公开刊行,破除迷信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