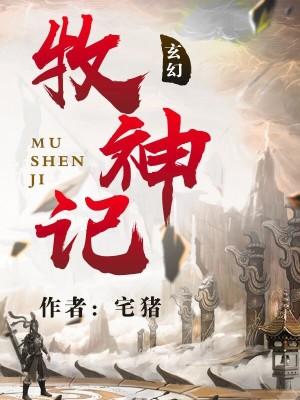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仙工开物宁拙孙灵瞳无弹窗笔趣阁全文 > 第440章 淘汰班积(第4页)
第440章 淘汰班积(第4页)
阿陶抬起头:“所以,只要还有人愿意为别人做饭,我们就不会真正死去?”
“对。”
守灶笑了,“而且,你们现在已经不只是做饭了。
你们是在重建‘家’的概念。
在这个流浪成常态的时代,你们用一碗粥告诉所有人:你可以没有星球,但不能没有饭桌;你可以失去亲人,但只要你还记得他们的口味,他们就还在陪你吃晚饭。”
话音落下,整座碗山开始发光。
那些空碗逐一盛满热腾腾的食物:一碗阳春面、一盘煎饺、一盅炖蛋……每一道都是某个逝者生前最爱的菜肴。
光芒汇聚成河,流向行灶号。
飞船表面浮现出万千面孔,他们笑着、说着、夹菜、碰杯,仿佛正在进行一场跨越生死的盛宴。
而此时,在宇宙另一端,新生殖民地孤儿院的孩子们围坐在食堂里,惊讶地看着餐盘自动加热,饭菜冒出袅袅热气。
“谁开的火?”
老师疑惑地检查电路。
一个孩子举起小手:“是我梦见的那个叔叔,他说今晚要请大家吃顿好的。”
与此同时,陈砚舟所在的废弃空间站内,那口铁锅再次微微震动。
他颤抖着手打开盖子,发现锅里的粥竟然还冒着热气,尽管电磁炉早已关闭多年。
他尝了一口。
咸的。
因为他哭了。
但这味道,和妻子当年煮的一模一样。
行灶号上,禾娘低声报告:“新增共鸣节点一百二十三个,覆盖十二个星域。
部分区域已出现自发性灶火复苏现象??有流浪者开始共享食物,有战俘营囚犯互相喂饭,甚至清灶会基层人员中有七人辞职,声称‘不想再抽走别人的回忆’。”
阿陶站在舷窗前,望着越来越远的饿乡。
守灶的身影已化作一颗星辰,悬挂在天际,像是一盏永不熄灭的灶灯。
“下一个去哪儿?”
禾娘问。
阿陶摸了摸肩头的布偶,轻声道:“回地球。”
“什么?”
禾娘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,“地球?那颗死寂的母星?大气层崩解、地核冷却、生态圈彻底崩溃……那里什么都没有了!”
“不。”
阿陶摇头,“那里还有土。”
“什么土?”
“最后一片绿土。”
他闭上眼,想起《寻味录》里记载的一段话,“陈砚舟种下的稻种,埋在北极地下种子库废墟之下。
根据气象模型推演,若能在春季融雪期注入定向热量,配合特定频率的摇篮曲共振……或许能让它们发芽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