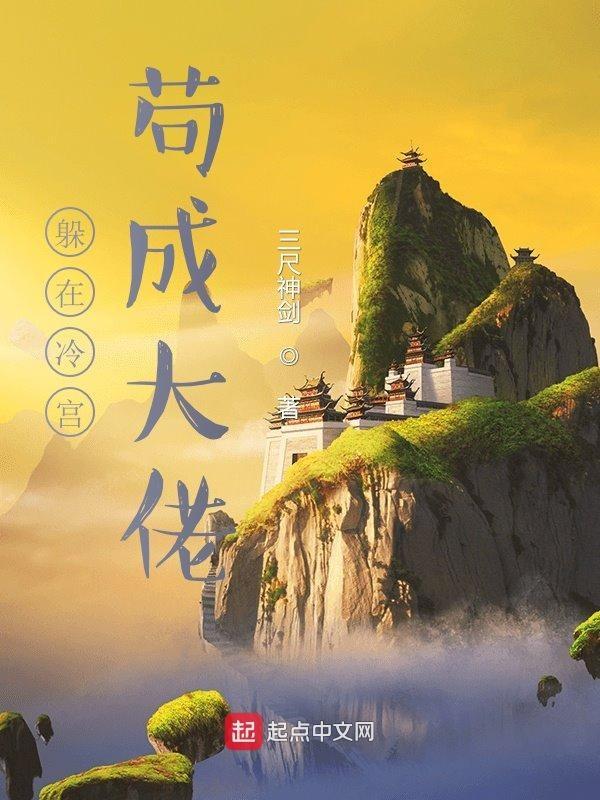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季明湿卵胎化小说TXT精校版 > 第1034章 耕父中官神(第6页)
第1034章 耕父中官神(第6页)
它存在于每一个敢于说“我不知道”
的谦卑里,存在于每一次“我可以解释”
的耐心里,存在于“我错了”
这三个字的重量里。
归真城没有纪念碑,没有雕像,也没有领袖画像。
唯一的纪念物,是一口普通的铜钟,挂在城中心的老梅树下。
它从不主动敲响,只有当有人完成一次真正的忏悔、一次深度的倾听、或一次打破沉默的勇气之举时,才会自发震动,发出一声清越悠长的鸣响。
有时一天响三次,有时十天也不响一次。
人们学会了等待。
而每当钟声响起,无论身处何地,所有人都会停下脚步,望向声音的方向,轻声说一句:
>“谢谢你,让我听见了真实。”
多年以后,当新一代的孩子长大,他们已无法想象曾经有一个时代,人们不敢说自己痛、不敢承认自己错、不敢问“为什么不可以不一样”
。
对他们而言,说话就像呼吸一样自然,倾听如同饮水一般本能。
但在每个入学第一天,先生仍会带他们来到梅树下,指着那口铜钟说:
>“这钟不会永远响下去。
它依赖人心中的诚实活着。
哪天若它沉默了,不是坏了,而是我们又开始说谎了。”
>“你们的责任,不是让它响得更久,而是让自己配得上它的声音。”
季明老了。
他坐在启言井边,白发苍苍,目光却依旧清澈。
苏渺渺靠在他肩上,两人静静看着一群孩子在草地上放风筝。
那些风筝不再是纸鸢,而是由心念编织而成的光影之翼,形状各异:有流泪的眼睛,有张开的手掌,有一本书正在燃烧却又重生。
一个小女孩跑过来,递给他一片梅瓣,上面写着稚嫩的字迹:
>“爷爷,我今天告诉老师我不喜欢她的课。
她说谢谢我诚实。
钟响了哦!”
季明笑了,接过梅瓣,轻轻夹进《启言录》最后一页。
他知道,弥从未离开。
她活在每一次颤抖却坚持说出的话语里,活在每一滴为陌生人流下的泪中,活在明知会被伤害仍选择相信的瞬间。
湿卵胎化,不是终点。
它只是让人类终于有资格,踏上成为“人”
的漫长旅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