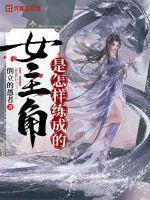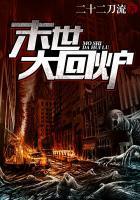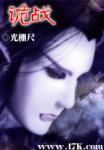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太太请安分 > 第202章 知难而退(第1页)
第202章 知难而退(第1页)
宁梦瑶突如其来的一句话令骑行中的少年陷入到了沉思。
他不清楚对方为什么会主动选择与自己搭话。
毕竟二人相识的时间虽不算太长,可在多次共同在场的情况下,也几乎没有像模像样的交流过。
本。。。
夜色如墨,却并不沉寂。城市在低语,巷口的风穿过老楼之间的缝隙,带着潮湿的砖墙气息与远处便利店飘来的面包香。沈如枝坐在工作室的窗台上,脚踩着暖气片,手里捧着一杯早已凉透的茶。电脑屏幕还亮着,是《无名者之光》项目第一期的剪辑草稿??那位修收音机的老人,名叫周伯,七十八岁,独居在城南一条即将拆迁的老街。他耳朵不好使,可手却灵巧得像能听见电流的声音。镜头里,他戴着放大镜,用镊子夹起一颗比米粒还小的电容,轻轻放进电路板上。“我修了一辈子收音机,”他说,“现在没人听了,可我觉得,声音不能断。”
刘松砚推门进来时,带进一阵冷风。他脱下外套,看见她蜷在窗边的样子,轻步走过去,把一件厚毛毯披在她肩上。“又熬夜?”他低声问。
“睡不着。”她转过头,眼神清亮,“我在想周伯说的那句话??‘声音不能断’。我们拍的是人,可其实,我们在找的是一种延续。一种不会因为被遗忘就消失的东西。”
刘松砚没说话,只是坐到她身旁,目光落在屏幕上定格的画面:老人布满皱纹的手握着一把螺丝刀,灯光下,金属反着微光,像某种仪式的圣器。
“你知道吗?”他忽然开口,“昨天小满打电话给我,说福利院有个孩子开始模仿她的手语动作了。不是被动地学,是主动比划。他画了一幅画,送给她,上面是一个大人牵着小孩,站在阳光里。他在下面歪歪扭扭写了三个字:‘我要光’。”
沈如枝怔住,眼眶慢慢红了。
“她说,那一刻她终于懂了你为什么坚持要做这些片子。”刘松砚望着她,“不是为了感动谁,也不是为了让世界改变。而是为了让那些从未被听见的人,知道他们并不孤单。”
窗外,天边泛起鱼肚白。新的一天正在悄然降临。
第二天上午,《无名者之光》首映会在市图书馆举行。场地不大,但座无虚席。有残联工作人员、高校社会学教授、公益组织代表,也有普通市民。甚至来了几位曾在《她们的名字》巡展中出现过的主人公??陈志远抱着女儿坐在前排,林婉秋拄着拐杖静静聆听,李秀兰由女儿搀扶着到场,看到大屏幕上自己的身影时,她用手语对身边人说:“原来我也能发光。”
影片开始前,沈如枝站上台,声音平静却有力:“三年前,我还在为一个广告提案焦头烂额。那时我以为,成功就是拿到大单、赚够钱、住进顶层公寓。直到有一天,我走进一家盲人按摩店,听到那位师傅对我说:‘姑娘,你走路太快了,心会累。’”
台下安静极了。
“从那天起,我开始慢下来,去看那些被忽略的脸,去听那些沉默的声音。今天我们带来的这部片子,主角不是英雄,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。他是一个修收音机的老人,一生未曾成名,也没挣过大钱。但他坚持了一件事??让声音继续存在。”
灯光暗下,画面缓缓展开。
镜头从清晨的老街切入:雾气弥漫,石板路上积着昨夜的雨水。一只布满老年斑的手推开木门,吱呀一声,打破寂静。周伯走出屋子,弯腰捡起门前的牛奶瓶,顺手擦了擦门框上的灰尘。他的生活极其规律:六点起床,煮一碗阳春面,听一段老电台的戏曲节目,然后打开那间不足五平米的“修理铺”。
铺子里堆满了老旧电器??收音机、录音机、老式电话机,甚至还有台八十年代的黑白电视机。墙上挂着一块手写招牌:“修声匠人,修得了机器,也修得了记忆。”
一位老太太拎着一台破旧的半导体来修,说是丈夫临终前最后听的一首歌还没听完。“他走得太急,连关机都没来得及。”她说着,眼泪掉了下来。
周伯接过机器,默默检查线路。三天后,他亲自送到老人家中。当熟悉的越剧唱腔再次响起时,老太太捂着嘴哭了整整十分钟。
“我不是在修机器,”他在采访中说,“我是在帮人找回声音里的亲人。”
影片结束时,全场静默数秒,随后掌声如潮水般涌起。有人抹着眼泪起身离席,有人久久坐着不动,仿佛仍在回味那些细碎却深沉的画面。
散场后,一位年轻女孩拦住沈如枝,声音颤抖:“我爸爸是个殡仪馆化妆师……他从不让我跟同学提起他的工作。他说,别人会觉得晦气。但我看过你们的片子,我想告诉你们,他也值得被看见。”
沈如枝握住她的手,点头:“我们会去的。”
当晚,团队召开复盘会议。池锦禾激动地说:“这片子必须上线!不只是纪录片平台,还要进校园、进社区放映!”
谢晨广则更现实些:“热度有了,但我们得考虑后续内容的可持续性。下一个拍谁?怎么保证每集都有同等的情感力量?”
沈如枝翻开笔记本,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众筹留言中的真实故事。她指着其中一条:“这个??内蒙古草原上的邮递员,骑马送信三十年,一个人负责六个嘎查。他说最怕冬天,雪太大,信会被埋住,可牧民等着汇款单、录取通知书。”
“还有这个,”刘松砚接话,“云南边境村的小学代课老师,一个人教四个年级,每天翻两座山来上课。学生家长说,她是‘照亮山路的月亮’。”
“我们就从这两个开始。”沈如枝合上本子,“不再局限于城市,要走向更远的地方。”
计划迅速推进。两周后,他们启程前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。草原辽阔,冬风凛冽。当地交通不便,手机信号断断续续,但他们坚持全程跟拍。
那位邮递员叫巴图,蒙古族,五十多岁,脸上刻着风吹日晒的痕迹。他骑一匹枣红色老马,背着鼓鼓囊囊的邮包,在雪原上踽踽独行。有时一天只能送三封信,但每一封都郑重其事地交到收件人手中。
有一幕令人动容:一位独居老人收到儿子寄来的照片,颤抖着双手展开,看着看着突然跪倒在地,朝着南方磕了个头。“我儿子在外地打工,五年没回来了……他还记得我生日。”
巴图默默站在一旁,摘下帽子,低头致意。
拍摄结束那天,暴风雪突至。车子陷在雪地里动弹不得。巴图二话不说,牵着马在前面探路,一步一陷,硬是带他们走出了困境。临别时,他用生涩的汉语说:“你们拍我,我不重要。但请让更多人知道,这里有人等信。”
回程途中,沈如枝在颠簸的车上写下日记:“我们总以为信息时代已无需等待,可在这片土地上,仍有人靠一封信维系亲情,靠一张明信片确认存在。巴图不是快递员,他是希望的摆渡人。”
一个月后,《无名者之光》第二、第三集同步发布。点击量再次破百万。评论区刷屏:
【我爷爷也是乡村邮递员,看完哭了一整晚。】
【原来这个世界还有人这样活着,真好。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