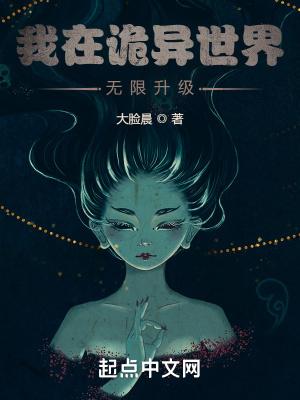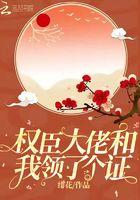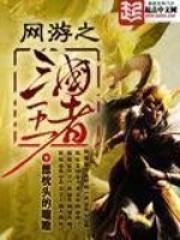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你们管邪修叫天才? > 90傻子(第3页)
90傻子(第3页)
>史非书,乃行;名非字,乃命。”
女子笑了。
她将灯递向陈吏:“接下来,交给你了。”
“我?”陈吏怔住。
“你是陈砚之的儿子,是第一个真正读懂人皮书的人,是你父亲用生命写下的最后一个字选择了你。”她目光温柔,“这盏灯,只会照亮愿意承担责任的人。”
陈吏颤抖着接过灯。
刹那间,脑海中闪过无数画面:父亲临终前刻字的手指,母亲抱着婴儿跳井的身影,村中老人偷偷教孩童唱禁歌的夜晚,阿石在雪地里挖出第十块残碑时的狂笑……
他明白了。
真正的历史,不在书里,不在碑上,而在人心的选择之中。
他举起灯,面向忘川府,朗声道:
>“我,陈吏,生于永昌五年腊月十七,父陈砚之,母柳氏,妹夭折于饥年。
>我曾以为读书可明理,后来才知,有些理,要用血来写。
>今日我在此立誓:宁可身死,不使真言湮灭;纵令万劫,不负此心昭昭!
>若有人问我姓名由来??
>吏者,非官也,乃记也!
>我名为吏,便是为史而生!”
话音落,灯焰暴涨百丈,化作一道光柱直冲骨城核心。
孟扶光终于变色:“不可能!凡人怎能承载‘史承之火’?!”
“因为你忘了。”陈吏眼中泪光与火光交织,“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”
光柱中,浮现万千虚影??那些曾献出手稿的老者,捧出铁牌的铁匠,痛哭忏悔的周怀恩,甚至包括裴仲言临死前悔恨的脸……全都汇聚成一条奔腾长河,撞向忘川府。
咔嚓!
整座骨城从中裂开,执笔之鬼纷纷挣脱枷锁,仰天长啸。有的化作风烟消散,有的跪地痛哭,有的则拾起碎片上的文字,拼凑成一本本残卷,投入忆桃原古井。
孟扶光站立不动,任由裂缝逼近。
“你恨我吗?”他问陈吏。
“我怜悯你。”陈吏答,“你一辈子都在替别人写历史,却从没为自己活过一天。”
孟扶光嘴角微动,似想笑,却吐出一口黑血。他的身体逐渐透明,最后只剩下一枚玉簪坠落尘埃。陈吏拾起一看,簪头刻着两个小字:**归真**。
风起,吹散了最后一缕黑雾。
倒悬之城缓缓沉入冰渊,伴随着一声悠长叹息:“愿来世,不做执笔者,只做读史人。”
天亮了。
阳光第一次毫无遮拦地洒在忆桃原上。桃花重新绽放,不是虚假的粉艳,而是带着霜痕与伤疤的真实之美。
十八具棺椁沉入井底,与其他百五十三具合葬。井口封石刻字:“千灯照夜,一人不孤。”
护史同盟各自归乡,但他们带走的不只是记忆,还有使命。每人领走一份《桃烬录》副本,藏于家中药柜、灶膛、祖坟碑底,约定十年一传,代代不息。
阿石临行前,递给陈吏一把铁锹:“等我把北方剩下的碑都挖出来,再来找你喝酒。”
青禾也将启程南下,去建立第一所“识伪学堂”。临别时,她留下一句话:“以后的孩子,不该靠做梦才能知道真相。”
女子最后看了一眼这片土地,提灯转身,身影渐渐淡去。
有人说她回到了深山古观,继续守护灯火;也有人说她化作了风,游走于民间说书人的茶馆之间;更有人说,每当有人深夜翻阅禁书时,窗台上总会多一盏不会熄灭的青玉灯。
多年后,新帝登基,废清忆司,设“实录院”,广征民间史料。朝堂之上,首次公开讨论“永昌之殇”。
一位年轻御史起身奏道:“臣请陛下,将每年腊月十七定为‘记日’,全国休政一日,百姓可自由讲述往事,学子须诵读《灾异志》序篇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