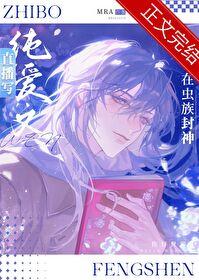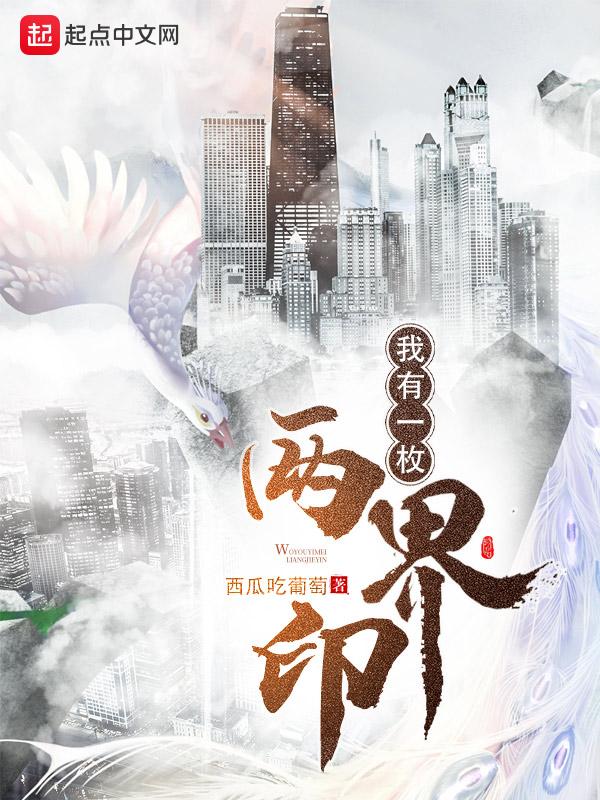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状元郎 > 第三五九章 卧龙凤雏(第1页)
第三五九章 卧龙凤雏(第1页)
若遇到特别出色的试卷,同考官可予以‘高荐’,即强力推荐。
这类高荐试卷,主考官通常极少驳回,多会给同考官个面子。
因为一旦这种卷子被刷下来,同考官往往会再次推荐,这一行为被称作‘抬轿子’。。。。
苏录扶着王阳明缓缓走出学宫街口,日头已偏西,余晖如金,洒在青石板路上泛出温润的光。街口早有家人等候,苏家老仆牵马提篮,见主子们出来,忙迎上前去。苏淡将考篮递与仆人,又取帕子给王阳明擦额上汗珠,口中轻声道:“七叔辛苦了,先坐车里歇着,咱们慢慢回。”
王阳明却不肯上车,只拄着苏录的肩喘息片刻,抬头望了一眼那巍峨的学宫门楼,忽而一笑:“我这一生,自弱冠应试,三十余年未断笔墨,今日方知,原来也有写不动的一天。”语气虽淡,却透着几分苍凉。
苏录低声道:“爹不必忧心,您已尽全力,儿辈自当承志。”
“我不是为功名忧。”王阳明摆摆手,目光落在苏录脸上,“我是怕误了你们的前程。若我名列劣等,你身为子侄,难免受牵连。虽说科试不似乡会那般严苛,可终究是官府定品,一丝污点,都可能埋下祸根。”
苏录心头一紧,这才明白父亲真正所虑。科试虽仅为资格之考,然其成绩仍记入档案,上报礼部备案。若父被黜落,虽不至于直接牵连子孙,但在将来举荐、授官之时,必为人所诟病。尤其苏录如今声名鹊起,更易遭人攻讦。
他正欲宽慰,忽听身后传来一阵喧哗。
回头一看,却是几位同窗簇拥着一名秀才走出考场,那人面带红光,手中试卷高举过顶,朗声道:“此题不过尔尔!我破题便用‘道契于心,行藏非外’八字,起讲三层递进,比对工稳,收束有力,诸君以为如何?”
众人附和称妙,其中一人笑道:“张兄此文,若不得优等,天理难容!”
苏录认得此人,乃泸州府学廪膳生员张文?,素来自负才学,院试时曾与苏录同场竞技,结果名落孙山。今见他如此张扬,心中不免冷笑??科试题目重义理阐发,非徒逞文采者所能胜出。此人破题尚可,然若无深层体悟,终难登堂入室。
但他并未多言,只轻轻摇头,扶着王阳明上了马车。
归途中,夕阳熔金,晚风微凉。苏录坐在车辕旁,望着远处江流滚滚,思绪却早已飞回考场之中。那一日的心流状态,至今仍在他胸中激荡。他隐约觉得,自己似乎触到了某种前所未有的境界??不是简单的文章精进,而是精神上的跃迁。
就像阳明先生所说:“心即理也。”当他不再执着于“写出好文章”,而是真心以圣贤之道自省、教化时,笔下自然流淌出沛然正气。那种感觉,仿佛不是他在作文,而是“道”借他的手在书写。
“莫非……这便是‘致良知’的初兆?”苏录喃喃自语。
车轮辘辘,回到家中已是掌灯时分。苏家宅院不大,但收拾得整洁雅致,庭院中种了几株桂树,此时花苞初绽,暗香浮动。仆妇们早已备好热水与汤食,王阳明被搀扶至厢房躺下,由苏淡亲自煎药侍奉。
苏录则径直走入书房,取出稿纸,将白日所作四书文逐字誊抄一遍。墨迹未干,常厚纨竟亲自登门拜访。
“听说你爹今日考场不适?”常厚纨进门便问,神色关切,“我特地来看看。”
苏录连忙起身相迎:“劳烦大宗师挂怀,家父只是久坐成疾,并无大碍。”
“唉,年纪不饶人啊。”常厚纨叹息一声,在案前坐下,接过苏录誊好的文章,细细读来。
烛火摇曳,映照着他清瘦的脸庞。起初他还边读边点头,待看到后半篇“共抱德恒垂千古”一句时,忽然身子一震,双目睁大,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
“这……这不是普通的代圣人立言!”他声音发颤,“这是……这是‘以心契道’!你……你竟已通此境?”
苏录一怔:“学生不知所云。”
“你还装傻?”常厚纨激动得几乎拍案,“你以为这种文章是谁都能写出来的吗?破题不落窠臼,承题如泉涌出,起讲层层推进,全篇不见雕饰,却字字含道!尤其是这句‘舍非弃世,用岂求荣’,简直直追横渠先生‘为天地立心’之气象!”
他死死盯着苏录:“你老实告诉我,是不是萧提学亲授你心法?还是……你真跟阳明先生学到了什么秘诀?”
苏录沉默片刻,方才低声道:“学生确曾随老师游龙场,夜宿山洞,观星听泉,也曾见老师静坐七日不语,忽而大笑,泪流满面,自称‘吾道得矣’。彼时我不解其意,只觉玄妙。直到近日,方有所悟。”
“悟什么?”
“悟到??文章本无形,唯心所现;道不在书,而在吾心。”苏录缓缓道,“昔者孔子谓颜渊‘用之则行,舍之则藏’,并非教人投机避世,而是说无论身处何境,只要守得住本心,便是行道。若心为外物所役,则纵使身居庙堂,亦是‘藏’而不‘行’。”
常厚纨听得浑身一震,久久不能言语。
良久,他才长叹一声:“我教书三十年,阅卷无数,原以为天下英才尽在我掌握之中。今日方知,真正的圣贤种子,早已不在经生堆里,而在那些敢于直面本心的人身上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