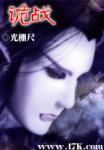棒子文学网>状元郎 > 第三四八章 王府文会(第1页)
第三四八章 王府文会(第1页)
苏录等人穿坊而过,但见道路两侧竹篱疏朗,芝兰吐香,大大冲淡了王宫内廷的威严肃穆。
行至深处,眼前豁然开朗,但见一湾泮水如镜,垂柳依依拂水,荷花亭亭玉立,岸畔太湖石叠出玲珑峰峦,一道九曲石桥卧于水。。。
苏泰咧嘴一笑,露出一口白牙,泥巴还没洗净的脸上满是得意:“老师,这回可真是您教得好!光靠蛮干不行,得动脑子。”王守仁笑着摇头,拍了拍他的肩:“是你自己悟得透。学问之道,不在死记硬背,而在格物致知。今日你格的是砖,明日便可格天下万事。”众人闻言皆肃然,连一向嬉笑的苏录也收了脸上的轻佻,低声念道:“格物致知……原来竟是这般用法。”
奢云珞从贵州城归来时,正撞见这群人围坐在新砌的青砖院墙下谈天说地。她跳下马背,罗罗武士们卸下几大包药材、布匹与笔墨纸砚,还有两坛陈年米酒。苏泰一见便嚷嚷起来:“哎哟,大小姐这是把外公家底都搬空了吧?”奢云珞白他一眼:“少贫嘴,这些东西可是我求了三天才讨来的,你倒说得轻巧!”说着将一卷文书递给王守仁,“外公让我转交先生,说是些地方志和前朝典籍,或许对您的讲学有用。”
王守仁接过,双手微颤,眼中竟泛起一层薄雾。他缓缓展开,只见纸页泛黄,字迹工整,乃《贵州通志》残卷,另附有《水西安氏谱牒》与《西南驿道考》。他轻抚纸面,低声道:“安宣慰竟肯以如此重宝相赠,老夫何德何能?”奢云珞笑道:“外公说了,阳明先生若能在龙场开坛讲学,便是为我贵州文脉点灯,这点东西算什么?”王守仁深深一揖,不再言语,只将书卷抱于怀中,如同护着初生婴孩。
当晚,众人围炉夜话。火堆噼啪作响,映得人脸忽明忽暗。奢云珞将杨斌升任四川按察使之事又细说一遍,末了叹道:“如今他是朝廷命官,手握司法大权,若真要对付我娘,一道公文便可置之死地。”苏录听得怒不可遏,一拳砸在地上:“岂有此理!土司僭越职权限,还当上了一省臬台?这刘瑾究竟要把大明搅成什么模样!”王守仁却只是沉默良久,方道:“非常之时,行非常之事。刘瑾擅权,朝纲崩坏,然天理自在人心。杨斌虽得高位,若行事不义,终将自取其祸。”
“可咱们不能等他自取其祸啊!”奢云珞急道,“我娘如今闭门谢客,日夜修缮赤水河堤坝,只为早日打通与水西的商路。可工程浩大,银钱不足,工匠又少……”她顿了顿,目光扫过众人,“我想请先生写一封荐书,让我去贵阳府衙借些款项,哪怕只是暂借,也好过坐以待毙。”
王守仁眉头微皱:“你一个女子,出入官府本就艰难,何况如今刘瑾党羽遍布,稍有不慎便会惹来杀身之祸。”奢云珞倔强地扬起头:“我不是为自己去,是为了整个奢家,为了母亲,为了将来这片土地上的百姓不再受杨家欺压!先生常说‘知行合一’,若明知该做却不做,那还算什么知?”
此言一出,四座皆静。王守仁凝视着她,良久,终于点头:“你说得对。明日我便为你修书一封,托付给贵州提学副使席书。此人虽未公开与我往来,但曾私信称仰慕心学,或可相助。”苏泰立刻起身:“我去准备笔墨!”苏录也道:“我陪大小姐同去,万一官府刁难,也好有个照应。”王守仁摆手:“不必,此事须低调行事。云珞一人前往即可,带上两名罗罗武士足矣。你们去了反倒惹人注目。”
次日清晨,王守仁亲手写下荐书,字字恳切,言及奢氏修河利民之举,赞其“深明大义,心系苍生”,并称奢云珞“才识过人,不让须眉”。书毕,他又取出一枚旧印,乃是当年在兵部任职时所用私章,盖于文末,郑重交予奢云珞:“此印尚有些许分量,若遇阻滞,可出示以示身份关联。”奢云珞双手接过,眼眶微红,低声道:“先生厚恩,云珞永世不忘。”
三日后,奢云珞再赴贵阳。此次她换上素色儒裙,发髻高挽,俨然大家闺秀模样。两名罗罗武士扮作仆从,悄然随行。抵达府衙时正值午时,提学副使席书正在堂上批阅公文。听闻有女子持阳明先生荐书求见,席书颇感惊讶,命人引入。
奢云珞进厅,盈盈下拜:“晚辈奢云珞,奉阳明先生之命,特来拜谒大人。”席书见她举止端庄,谈吐不凡,又见荐书笔力雄健,情真意切,心中已有几分好感。细问之下,得知她母主持修赤水河工程,旨在贯通黔北水运,便利民生,不禁动容:“此乃利国利民之举,本当支持。然财政紧绌,府库空虚,实难拨款啊。”
奢云珞不慌不忙,从袖中取出一份图纸,正是苏泰依地理形势所绘的《赤水河道整治图》,上有详细测算与工期预算。“大人请看,此工程分三期进行,首期仅需三千两白银,便可疏通主航道三十里,使小船通行无阻。届时商旅云集,关税增收,不出两年便可回本。若大人愿贷此款,奢家愿以田产抵押,并承诺五年内还清本息。”她说得条理清晰,数据详实,席书越听越是惊奇。
沉吟片刻,席书道:“阳明先生向来不轻易荐人,你既得他亲笔举荐,想必非同寻常。这样吧,我可奏请巡抚,暂拨一千两作为试助,若首期工程见效,再议后续拨款。”奢云珞大喜,连忙叩首:“多谢大人成全!”席书摆手笑道:“不必谢我,若真能造福一方,倒是我要谢你才是。”
归途之中,奢云珞心情畅快,一路哼着山歌。苏录派来接应的探子早已等候多时,见她安然归来,立即飞马回报龙场。王守仁闻讯,抚掌而笑:“云珞此行,可谓智勇双全。”苏泰却挠头道:“老师,咱们这边刚烧出青砖,正准备盖学堂呢,可钱粮还是不够啊。”王守仁望向远处群山,悠悠道:“世间万物,皆有其时。心不动,则万事不扰;心若动,则处处机缘。只要我们守住本心,何愁大事不成?”
果然不出半月,席书派使者送来第一批银两与建材清单,另附书信一封,言明朝廷有意在西南推行“屯田养学”政策,若龙场驿能建成书院,或可申请专项资助。王守仁大喜,当即召集众人商议建校事宜。苏泰主动请缨:“我带人去山上伐木,再烧一批砖瓦!”苏录则道:“我去联络附近村寨,招募愿意读书的子弟,免他们束?!”常毅提议:“不如设个‘劳学结合’制度,学生一边读书,一边参与建校,既能磨砺意志,又能减轻开支。”
王守仁一一采纳,并亲自拟定书院名称??“龙冈书院”。他在石碑上亲题四字,笔力遒劲,气势恢宏。苏泰看着那四个大字,忽然跪倒在地,泪流满面:“俺爹娘一辈子没读过书,临死前还说‘要是娃能识几个字,就不算白活’……如今咱也能有学堂了!”王守仁扶起他,声音哽咽:“安之,你可知为何我坚持在此荒僻之地办学?正因为这里最缺光明。一个人的觉醒,可以唤醒一家;一家的觉醒,可以带动一乡;一乡的觉醒,终将照亮整个西南!”
建校工程全面启动。每日清晨,鸡鸣未歇,众人已挥锄动斧。妇女们送来饭菜,孩童们搬运碎石,连七八十岁的老人都拄着拐杖来帮忙夯土。三个月后,三间青砖瓦房拔地而起,屋前立着一块黑漆匾额,上书“龙冈书院”四个金字,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开学当日,王守仁身穿粗布长衫,立于讲台之上。台下坐满百余名学子,有汉人、苗人、彝人、仡佬人,男女皆有,年龄从十岁至五十不等。他深吸一口气,朗声道:“诸位,今日我们在此开讲,不为科举功名,不为升官发财,只为明白一件事??什么是人?什么是心?什么是良知?”
全场寂静无声。
“天地虽大,但有一念向善,心存良知,虽凡夫俗子,皆可为圣贤!”他声音洪亮,穿透山谷,“我王守仁被贬至此,不是失败,而是重生!因为我终于明白,道不在庙堂之高,而在民间烟火;不在经书字句,而在百姓疾苦!今日起,我们要做的,就是让每一个走进这扇门的人,都能找回自己的良知!”
掌声雷动,经久不息。有人流泪,有人跪拜,有人激动得浑身颤抖。苏泰站在人群最后,紧紧攥着拳头,心中默念:“哥儿,你看见了吗?咱家也有学堂了!”
夜深人静,王守仁独坐书房,提笔撰写《教条示龙场诸生》。烛火摇曳,映照着他清瘦的脸庞。他写道:“诸生相从于此,甚盛心也。恐无能为助,惟励所志而已……立志者,心之所向也;勤学者,身之所行也;改过者,省察之功也;责善者,朋友之道也……”笔锋流转,字字千钧。
窗外,一轮明月高悬,清辉洒落书院檐角。远处传来悠扬的芦笙声,夹杂着孩童背诵《大学》的稚嫩嗓音:“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……”声音渐远,融入山风,仿佛天地共鸣。
与此同时,千里之外的播州城中,杨斌端坐堂上,手中握着一封密报。他冷冷一笑,将纸投入火盆,火焰瞬间吞噬了“龙场书院”四字。身旁幕僚低声问道:“是否派人去查?”杨斌摆手:“不必。一个贬官,在穷山恶水办个破学堂,翻不起浪来。眼下要紧的是,盯住奢家修河进度,等他们耗尽财力,再一举吞并!”幕僚谄笑道:“大人高明,届时水西、播州连成一片,西南半壁,尽入囊中矣!”
然而他不知,就在同一时刻,安贵荣已在水西密召族老,宣布重启“九驿通商”计划,并下令各寨储备粮草、训练武士。他对心腹道:“杨斌得意太早。阳明先生在龙场讲学,那是给整个西南播下火种。火势一起,谁还能挡?”
数日后,一名神秘僧人穿越崇山峻岭,抵达龙场驿。他手持一封密信,直奔书院,面见王守仁。拆信一看,竟是时任南京吏部尚书杨一清所书:“闻君在黔讲学,振奋人心。今刘瑾专横日甚,然众怒已积,不久必败。君宜保重身体,积蓄力量,待时而动。天下之大,终需真儒出而救世。”
王守仁默然良久,将信焚于灯下,轻叹一声:“时机未至,然火种已燃。”他转身望向窗外琅琅书声,嘴角浮现出一丝坚定笑意。
风雨欲来,而龙场的灯火,彻夜未熄。